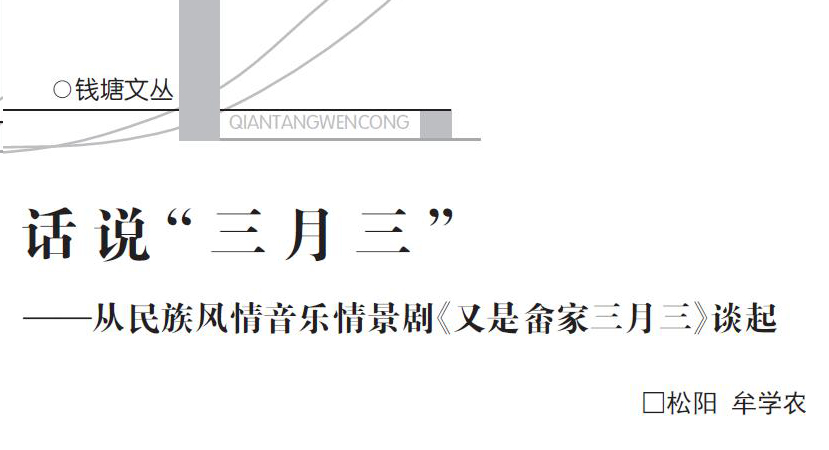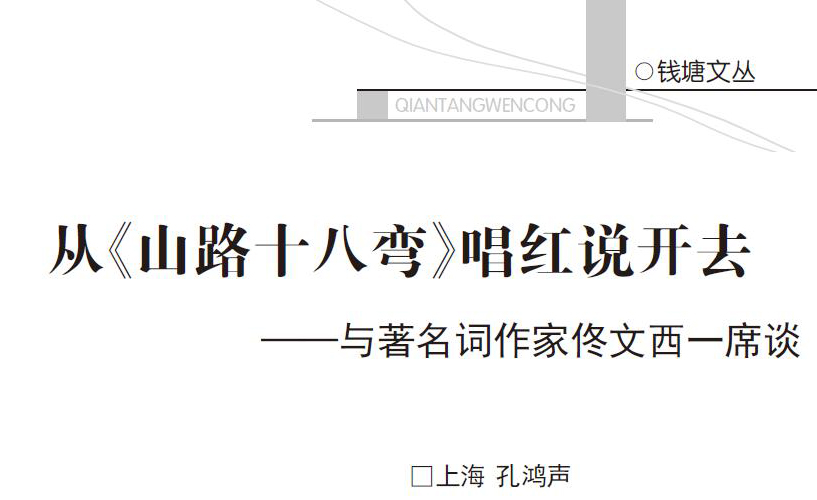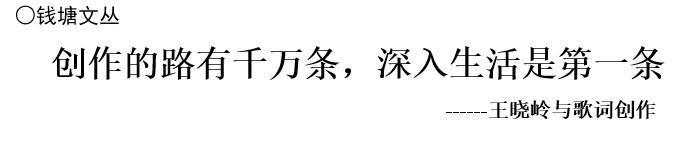论现代歌词与新诗的区别

歌词和诗同属以抒情为本的语言艺术。《舜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的话,《乐记》对此作了解释:“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这里的“歌”即歌词。由此可见中国传统诗学中早就认定歌词是诗歌家族的成员了。陆正兰在《歌词学》中说:“整整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诗在歌词与徒诗之间摇摆的历史。”还指出:“徒诗与歌词不断地转换位置:每当一种诗的样式充分发展,‘内转’到无可再转,需要新的形式时,诗就回过头来找歌曲,把歌的音乐性转移到诗歌语言内部的音乐性上。”(1)这种说法很有代表性。有人进一步发挥,认为中国新诗滥觞于现代歌词。钱仁康在《学堂乐歌考源》中就认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学堂乐歌”是“新诗的萌芽”;“许多乐歌的歌词作者苦心突破旧体诗的格律,试图开创新的诗歌语言和形式,从他们所作的歌词中,可以看到新诗发展史的轨迹。”(2)以这样的看法去认识新诗发生的根源,当然犹待文学史家作深入探讨,但陆正兰、钱仁康的这种提法值得重视,他们至少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歌词与徒诗都是诗歌家族的成员,现代歌词与新诗可归入一个范畴,即诗学范畴。不过也不能不看到歌词有其身份的特殊性,它的存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附于音乐。正是这种依附性,使歌词与徒诗既有一致的本质属性,却又在一些体现本质属性的关键问题上存在着区别。特别由于现代歌词对音乐的依附随着传播手段的飞速发展而日趋严重,这种区别也就更为显著。故本文打算通过审美基点、结构方式、意象表现、语言策略、节奏类型这五个方面,对现代歌词与新诗的区别作一考察。
一、审美基点:心灵独白与广场呼应
歌词与徒诗都是直接从实际生活感受出发来抒情的,或者说:主体把心物感应而得的情绪,提升为知觉情感来展开抒情,是歌词与徒诗共同具有的诗学属性。唯其如此,才使歌词创作不像音乐创作那样显现为抽象的、灵感突发式的表现,而像徒诗一样是对生活感受的具象反映。应该说:从实际生活感受出发的抒情作为歌词与徒诗共具的属性,是有其诗学本质意义的,因此这点也就成了二者带根本性的一致之处。但是,恰恰也是在这一方面,它们又因了审美追求的基点不同,而显出了关键性的区别;而反映在现代歌词与新诗上,这种区别尤甚。
同所有徒诗一样,作为以抒情为专职的新诗,就其终极而言是立足于“我”并以“我”为出发点去展开抒情的审美活动,可见新诗的抒情究其根本是一场自我表现;不论从哪一种人称出发构成的新诗文本,实在都是自我心灵絮语式感受抒发,一场自言自语以求得自娱的活动。雅可布森在《语言学和诗学》中提出“诗性即符号的自指性”。托多罗夫在《诗学》中说“符号不指向他物”。这两位西方符号学家所谓的“符号”即文本符号,所以“自指性”也好,“不指向他物”也好,意思就是诗歌那种直接从实际生活感受出发的抒情追求,虽然在文本中也可以显示为由第二人称的“你”或“你们”、第三人称的“他”或“他们”出发来展开,甚至也还可以表现出面对他者论述、祈求呼应的倾向,但最终也不过是诗人主体的自我心境反映。郭沫若在《学生时代》中回忆到自己写的《湘累》时说:“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就好像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3)这也足以说明:一切徒诗——包括新诗,其实都像《湘累》一样,是诗人的“夫子自道”——一场心灵絮语式独白。歌词的情况恰恰相反,其文本符号不属“自指性”,而总是指向他物的。以第一人称“我”出发展开抒情的极大多数歌词,其实是在进行群体表现,即群体相互间作感受交流式的情绪抒发,故歌词的抒情审美追求可以作这样的定位:这是一场我呼而求你应的呼应性活动。这里须要提一提“呼应”。《淮南子•道应训》中这样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就是呼应——一种群体情绪的交流。所以歌词的审美追求基点,就是这种有情绪互动意味的呼应。同徒诗所抒之情有较强个人化色彩不同,歌词所抒之情更多点大众化色彩;也同徒诗自我心灵絮语式抒情有较浑沌的潜意识成分不同,歌词群体呼应式抒情则有较清醒的意识成分。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认定:从所抒之情的质素而言,歌词比徒诗更多点理性的渗透,只有让主体的情绪经过理性化的知觉意识沉淀,成为可以让群体共通的情感,才能使歌词发生我呼而你应的鼓动性互动效应。
以上种种歌词与徒诗抒情审美基点上的区别,在现代歌词与新诗之间的关系中,显示得相当显著。亦门的诗《纤夫》和端木蕻良的歌词《嘉陵江上》是值得比较的。它们都以嘉陵江作背景抒情。从现象上看,《纤夫》中活动着的那一群纤夫——“我们”,是面临艰困险恶处境而展开抗战的一代中华爱国者集体形象的象征,实际上更是诗人满腔爱国之心的自我表现。绿原在《初记阿城》中谈到几十年后重读这首诗时,“仿佛又看见他赤着双脚、匍匐在荒凉的布满尖陵石块的河岸上,两肩被纤绳勒出深刻的乌紫的血痕,低着头拉住沉重的木船,一寸一寸地往前进……”(4)可见这首诗确是一场心灵絮语式的象征表现。《嘉陵江上》表现的是“我”——一个被敌人逐出家园、流落他乡的难民,徘徊在嘉陵江边,痛苦而不安地怀念着家乡,最后下决心要打回老家去——这样一段悲慨壮烈的心路历程。这个“我”当然可以说就是端木蕻良自己,他先经亡省之痛流亡关内,“七七”事变后再度流亡到嘉陵江边的重庆,所以歌词中流浪的情感完全可以属于他自己,但无论是“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乐和梦想”,或者“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甚或“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都让人感到这是一种主体以长呼而求听众应和的鼓动性行为,即使是主体自我的真实情感也已超越内心独白而成了广场交流的群体宣泄式情感;即文本中出现的“我”实质上成了千百万家破人亡、四处流浪而终于在国难家仇中觉醒、誓和敌人去拼到底的“我们”——中华儿女的总称。因此,现代歌词《嘉陵江上》也就以这种广场呼应式群体抒情表现特质,和新诗《纤夫》那种心灵絮语式自我抒情表现特质,在审美基点上显出了区别——纵使前者的抒情主体是“我们”,其实是“我”;后者的抒情主体是“我”,其实是“我们”。邹荻帆的新诗《无题》和薛柱国的现代歌词《我为祖国献石油》都抒发了一种为人民事业献身的激情,但它们在抒情审美基点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无题》从“我们”将会“扑倒在大风雪里”切入,展开一场献身壮丽事业的抒情,诗篇说:等到“我们”扑倒在大风雪里后,“我们温暖的血”会被吸收进“大树的根里”、“小草的须里”、“五月的河里”去,而“雪后的草原”将会坦露出一片美景:“天青/水绿/鸟飞/鱼游/风将吹拂着英雄的墓碑……”这种殉道者献身的激情虽以“我们”的身份抒发出来,其实是主体的诗人多少带点潜意识的自我表现,梦幻式的内心独白。《我为祖国献石油》抒发的是一个石油工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尖端项目——开采石油而献身的壮志豪情,歌词表现了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生动画面:“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然后这样抒发豪情:
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
我为祖国献石油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抒发这豪情的是“我”,但其实这是“我”呼求听众应和的群体情感表现。所以这里虽以“我”出场抒情,实质上是广大石油战士或者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我们”在抒情,在作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广场宣谕。还值得指出:从总体上看《无题》,以实质上的“我”体现的自我表现,《我为祖国献石油》以实质上的“我们”体现的群体表现显示着现代歌词与新诗在抒情审美基点上存在着不同以外,还在由此派生的“情”之质素上也有区别,《无题》梦幻式的心灵絮语是一场出之于潜意识的情绪表达,这种情绪有一定的浑沌性。《我为祖国献石油》宣谕式的广场呼应则是一种受制于理性意识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就显得明朗。这为歌词与徒诗在抒情审美基点上的区别加重了份量。
M•C•泰弟斯孝在探讨转化为歌词的那种“诗”时提出:这种“诗必须有一个‘有表现力的内核’”,这“内核”且须“表达一种‘灵魂的状态’”;并认为:“应该用一个完整、简洁、清晰、和谐然而没有过多文字的形式来表达这个‘内核’”,且这个“内核”还“应该给音乐留有一定的‘地盘’”(5)。这番话对我们颇有启发。能使歌词区别于徒诗的“内核”,也就是我们此处所说的抒情审美的基点。正是这个基点,才能“表达一种‘灵魂的状态’”。也正是一些能体现“完整、简洁、清晰、和谐”的结构、意象、语言、节奏体式,一旦同这个抒情审美基点相应合,也就能凸现歌词与徒诗“内核”上的区别,这是因为:作为“内核”的抒情审美基点对结构方式、意象表现、语言策略、节奏类型是天然地具有制约性的。
二、结构方式:起承转合与对称均衡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以“结构”取代“形式”,把文学结构看成是“内容和形式中依审美目的组织起来”(6)的现象。这“审美目的”结合歌词与徒诗来看,也就是上面所提及的那个抒情审美基点——“内核”。由此可见,歌词与徒诗在结构方式上的区别,和抒情审美基点之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福勒在《现代批评术语词典》中认为结构“即作品在展开中的统一性”(7),这意思指创作构思与文本构成统一于一个展开过程的关系网才算结构,比韦勒克、沃伦的谈结构要具体。把这两种文学结构思想结合起来,可以对结构有一个较辩证的认识:文本创造在展开中按特定审美目的而显示出创造诸因素间的统一性,谓之结构。以这样的认识来看歌词与徒诗的结构特征,也就会使我们超越外在谋篇布局的操作性而有了较宏观也较内在的结构思考。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徒诗的抒情审美基点既是主体的心灵絮语,也就会使欲抒之情具有一定程度的情境浸润性。情境浸润总显现为一个过程,即感觉情绪在多元想象的综合作用催动下发生的一场向情感的提升,而想象的综合又会使这场提升显出情绪从发生、展开、迂回再到高一层次上与起点相应合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显出了潜在的心灵逻辑,并在潜意识层次中把握到一个情绪内在推延律。这一点心灵推延律使徒诗在结构展开中获得了以起承转合为过程性标志的特征。所以徒诗大多以起承转合为结构表现方式。采用这种方式使徒诗的结构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一、徒诗的结构总是委婉曲折的,往往给读者以渐入佳境的感染性诱引;二、徒诗中情绪向情感提升的过程总是在起承转合的最后一个环节——“合”的推宕中完成的,推宕的结果则是对情感的真意化把握。值得指出:这两点情况都靠徒诗自身的感应机制达到,这反映着徒诗具有一种自足的结构完型。歌词的情况就不同了。歌词的抒情审美基点是群体广场呼应,欲抒之情具有一定程度的情调曳荡性。情调曳荡不显示为过程,而是原地踏步式的反复。这场反复来自于情绪激活的单色想象,正是这种单色想象,在不断重现中往往会跳过情感阶段而直接提升为理性。所以,单色想象的不断重现会使这场提升显出显在的意念印证,并在意识层次中把握到一个情意外在往复律。基于这一点,歌词在结构展开中也大多会以对称均衡作曳荡性标志。因此可以说,歌词是以对称均衡为结构表现方式的。采用这种方式使结构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歌词的结构总是率直单线的,往往给听众以一呼即应的刺激性诱引;二、歌词情绪的原地踏步、持续反复是其全部目的,它不求推宕效应,也无意于让情感升华以达到智性领会的更高境界。所以,从完成艺术的要求看,歌词的结构是残缺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自有歌词的苦衷:为的是留给音乐以一定的地盘,藉助音乐的感应机制去作推宕。所以歌词追求的只能是一种非自足的召唤结构。
现代歌词与新诗在结构方式上的区别也是显著的。
同样是表达一种对祖国的深情,艾青的新诗《我爱着土地》和张鸣西的歌词《祖国,慈祥的母亲》,在结构上就值得比较。《我爱这土地》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心灵絮语。它共十行,前八行是一节,最后两行另立一节。第一节的第一、二行是:“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是“起”。接着的四行是以四个意象来表现歌唱的内容:“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这些意象兴发出来的分别是苦难感、奋起感、战斗感和光明感,是“承”。接着第七、八行以“——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来了一个大转折,以死也要死在这块土地上的隐喻来进一层表达诗人对“土地”——祖国的爱的深情。最后是第二节的两行作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合”了——把“起”处活着时的爱和“转”处死后的爱合起来,把一缕生生世世永远眷恋着这片土地的感情推向更悠远深挚的境界。所以艾青的这首诗充分显示了结构上起承转合的特点,也以完型的结构反映出这首诗感应机制委婉曲折表现的自足。但《祖国,慈祥的母亲》却不同。它是这样的: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 ,
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
亲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
长江黄河欢腾着深情,
我们对你的深情。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
用那闪光的美妙青春。
亲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
蓝天大海储满着忠诚,
我们对你的忠诚。
这是“我们”的一场广场宣谕,一场以呼求应的群体情感交流,所追求的是直率的情绪感受的反复以获得鼓动效应。因此,反映在结构上,也就不讲究起承转合而追求诗节的对称均衡和诗行的对应复沓了。这样做,使歌词自身的感应机制很难说有推宕的功能,有关这方面它就让给音乐去完成了。还可举出两个抒发别离之情的文本来比较。先看吕剑的诗《打马渡襄河》是这样写的:“七百里风和雪,/我向东方,/打马渡襄河。/你从批把坪,/写诗来送行,/嘱我——/赶着春天去,/去丰收一个秋天……”这虽说是赠人的诗,却有慷慨踏上征途的心灵絮语意味。第一行是“起”,第二、三行是“承”,第四、五、六行是“转”,从“你”的视角对“我”抒情,于是有最后两行——“赶着春天去,/去丰收一个秋天……”以对未来的遐想来和第一行“七百里风和雪”相呼应,完成了一个可以向悠远人生感受推宕的“合”。所以这首诗是以起承转合的方式结构起来的,自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味。严华的《送君》广为传唱,其歌词共四节,每段都与百花有关,分别在洲、亭、江、路上“送君”,体现了一对情侣的恋之深、别之苦。前两节是:“送君送到百花洲,/长夜孤眠在画楼,/梧桐叶落秋已深,/冷月清光无限愁。//送君送到百花亭,/默默无言难舍情,/鸟语花香情难舍,/万分难舍有情人。”可以看出:这第一节是以景寓情,第二节是情的直抒。第三、四节是这样:
送君送到百花江,好花哪有百日香,
天边一只失群雁,独自徘徊受凄凉。
送君送到百花路,心比黄莲还要苦,
失意泪洒相思地,天也感伤雨如注。
这两节全是情景交融的抒情了。把这四节歌词综合起来看,它们所表达的是同一种情感,一种离愁别恨的反复吟唱。因此,结构也是对称均衡的,以期达到一种复沓效果。此处又显然显出了另一种形态的呼应,即主体把一种情思和相应的同类感兴意象作持续往复来形成一种情调,强行逼使听众的心灵与之应合。所以这种对称均衡的结构是非自足的,它以自己的残缺提供给音乐以施展旋律想象的“地盘”。由此可见歌词结构比诗要单纯、单一、单调,对歌词来说这是无损于它的存在价值的,因为它以对音乐的依附和辅助而显出价值了。所以读歌词《送君》,越读到后来越有重复、罗嗦、累赘之感,但装上音乐的旋律一吟唱,这种不佳的审美感觉也就不存在了。
三、意象表现:兴发感动与譬比印证
歌词与诗都通过意象来抒情。意象一般被说成是具体化的感觉,但并不全面。意象来自于感觉,那是无疑的。但意象之能用作抒情,乃在于它是从感觉起步而引起一场心物感应所致,这使它不只是停留在印象阶段,而显出兴发感动的功能来了。抒情的“情”就靠这种意象感发出来的。因此,说意象是具体化的感觉情绪也许更妥当一些。这里还值得注意三点:一、一个个意象孤立地看其实不过是人对外物的印象,这些印象让诗人在日常生活体验中把握住以后,会藏在记忆中,而一个抒情艺术创造者也总会有满脑子意象藏着,只等某一天这诗人或词人受到外在特定的刺激而生感觉情绪,这感觉情绪又激活了联想,促使主体从意象储蓄库里挑选其中可以应合的一个,与特定的感觉情绪一拍即合,才化成为创作过程中的意象。所以在诗歌家族中讨论的意象,只能是创作过程中的存在;二、人脑中作为外物印象的存在须转化为创作过程中意象的存在,这场转化的关键乃是必须让联想来挑选。联想是由事物唤起的类似的记忆,即经验与经验的呼应,故它的全称该是经验联想,经验属于知觉,这使得联想也有知觉理性渗透。创作过程中,让这样性质的联想去挑选出一个个受潜在创作意图遥控的、能与感觉情绪相应合的意象,就显示这是受制于知觉理性的一场活动,因此也必然会使意象成了有“意”为之地寻求而得且深印于记忆中的“象”,有鉴于此,我们方称它为“意象”。所以意象既具感发功能,也有以象显意的潜在性能;三、意象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不作静态存在,而显示为流动的趋势。诸意象的组合是这种流动趋势的具体表现。致于一个起点的意象找哪些其它意象组合,又如何组合,既受制于主体潜意识中的感应逻辑,也会受潜在的创作意图遥控。这使前者显出了直觉感兴,后者显出了知觉理性,而二者在意象组合中由于有这种双重制约,也就使意象组合体有感兴功能和意指性能的两面性。这三点情况反映着:意象及其组合体在正常的情况下都是这种两面性的有机融和。但世上的事物总是复杂的,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凡重直觉感应的意象及其组合体就偏于感兴;重创作意图的意象及其组合体则偏于意指。徒诗和歌词在意象表现上的根本区别,总体说就出在这种偏重上。徒诗的抒情审美基点出于诗人自我的心灵絮语,直觉感兴成分较浓,因此它的意象和意象组合体大都以直觉感兴化的具象来感发,这些具象形态的意象可以是不变形的,却也可以是变形的,特别是意象组合体,受潜意识层面的感应逻辑指派,竟让变形的和不变形的意象混在一起作不可思议的组接,更以怪异而无理的切割来强化组接的不可思议性,以期造成某种陌生化效果,来把意象及其组合体潜存的兴发感动功能强刺激出来,以期大幅度激活想象联想,使这场意象表现具有感兴式抒情审美效应,婉曲、含蓄,以致进入某种隐喻、象征的境界。当然,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隐晦、含浑,却倒也合于心灵絮语式抒情之本然特色。值得指出:意象抒情在徒诗中之所以能起这样大的作用,关键还是意象的感兴功能对激活想象联想特别有利,而想象联想的高度激活又反过来使意象更丰盈,感兴功能更强,进而又使意象抒情也得到更充分的表现。由此说来,徒诗的意象表现之能诱发读者进入特定的深邃境界,是靠徒诗自身的审美机制完成的。歌词的意象表现则是一场印证意象的抒情活动。由于歌词的抒情审美基点是群体表现,广场呼应,其知觉理性成分较浓,故它的意象和意象组合体虽也有直觉感兴化的具象来感发,但更多的情况是拿知觉譬比化的具象来印证。这些具象形态的意象大都不变形,尤其是意象组合体,受着意识层面的理性逻辑遥控,大多会让各个意象在分析、演绎链上井然有序地组接起来,在广场呼应的经验联想作用下,使这场意象表现具有了印证式抒情审美效应。这样做还能让情绪烘托与意旨印证的企图得以直率、明朗的表达。当然,这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浅白、直露以致缺乏余韵。但这倒是合于歌词群体呼应式要求的,因为广场宣谕必须是通俗化的,不避他人已用熟了的套语化意象,让听众一听就懂得印证的意图就算达到了目的,歌词本身余韵之不足则可以让音乐的旋律想象引起的感应来补足。由于音乐的旋律想象是抽象、朦胧的,歌词的这种意象表现以其明白、直露的情调铺垫与印证,还能起一种点化作用。附带提一提:正由于歌词对音乐的依附性,使它在意象抒情的表现机制上虽显出非自足的特性,但这是正常的,合于音乐文学的构成规律。
现代歌词与新诗在意象抒情的表现功能方面,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不妨拿舒婷的诗《思念》和严宽的歌词《蓝色的悠思》作个比较。《思念》可以说是一场完全用意象来抒发思念之情的心灵絮语,但又絮语得让一般人感到语无伦次,话不成腔。如第一、二节:“一幅色彩缤纷但缺乏线条的挂图/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它们一共八行,除了第七、八行是一个意象组合体,其余都是单个意象,互不关联地并置着。这些意象都有很强的感兴功能,感发出有情人总难圆梦相聚,只得无望地作着思念。它们又都远取譬,外在看,组接得南辕北辙,很难连起来,只靠同样感发着茫然而无奈的思念之苦所形成情绪气氛,才使它们统一起来。总之,这两节中意象的组接已陌生化到怪诞的地步,以致使其感兴功能因受到强刺激而越强化了感发效应。但这还不够。文本紧接着来了一次跨节跳跃,由此推出来的第三节是:
呵,在心的远景里
在灵魂的深处
从外象上看这一节和上两节也毫无关系,是突兀而出的,而且两个意象并置,初看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但深入品味,又会发现它们内在的感兴是一致的,暗示着上两节意象所感发出来的茫然绝望、无可奈何的思念系发自心灵最深处。总之,这样奇特的意象组合给予我们的印象是隐晦、含浑其事,主体思念之痛一点儿也不明说。要深入品味才能把握到。现代歌词《蓝色的悠思》的意象表现却完全不同。虽然同《思念》一样,也是用丰盈的意象来表现茫然而又无奈的思念之苦的,它这样写:
晚风微寒,夜莺深藏
春去徒留凄惶
北斗依稀,残月昏黄
暮色分外苍茫
这里已茁长了漫天的荒草
无言的小河里荻苇低低唱
夜长漫漫,你在何方?
旦夕不能相忘
这首歌词以春老之残象,月落之苍茫,远夜之孤栖,相思之漫长共融成一团惘然绝望、无可奈何的生存哀感。文本中不论“微风”、“夜莺”、“北斗”、“残月”,也不论漫天荒草、小河荻苇等等,都是已成套语的钝化意象,感兴功能是很弱的,但它们全围绕着生的哀感而存在着,又井然有序地按逻辑关系组接在一起。以此来印证生之哀感,凸现“你在何方?/旦夕不能相忘”的意图,很明确。没有一点婉曲含蓄的表白,全用明朗、直率的意象表现来印证一种欲求公众认同的意绪心态。歌词的广场宣谕式表现决定了它必须以单纯、集中的意象来作呼应式的抒情。现代歌词与新诗在意象表现上的这种区别,还很有意思地反映在当代人以同题《凉州词》写成的文本中。白耶的新诗文本《凉州词》是首汉式十四行诗,它以“66”式组合成对称的两节。全作是这样:“我有黄沙白草的美丽/威远楼声声羌笛/折杨柳里的望乡夜/冷月皎如雪/呵,孤城孤魂,残漏残叶/我的心纵使荒凉/但没有悲悒//我有征骑角弓的激昂/嘉峪关巍巍边墙/落日光中的烽燧路/笳声流成霜/呵,险山险水,异国异乡/我的心纵使荒凉/却更有悲壮。”这首诗采用了边城诸多阴寒、寂寞、荒芜、苍凉的感兴意象来反衬主体高昂的精神世界,而这些感兴意象则以反常情常理和外在无机的组接而给人以陌生新奇感,以致有激活想象联想特强的功能潜藏着,并导致整个意象组合体有内在情绪感兴的统一性。因此,这个诗文本的审美效应曲折隐晦得像一块压缩饼干,有高密度的意态心绪蕴含在里面,这使得读者不可能一读就懂,得慢慢品味,才能把握到内中丰富的蕴藏。毛瀚的现代歌词《凉州词》,意象表现有另一片风景。它的前两节是这样:“我那一首凉州词,/填不进你的采菱曲。/采菱曲呀是天籁,/总在潇湘月明里。//我那一坛渭城酒,/斟不进你的夜光杯。/夜光杯呀夜无眠,/不斟浊酒只斟泪。”这里的“凉州词”和“渭城酒”是核心意象,它们按合于经验联想逻辑地推延开去,让前者和“采菱曲”,后者与“夜光杯”拉上关系,表达出主体对江南春境界的怀恋和对边塞生态的哀感,意象组合体有机、富有层次感。随即是副歌式的第三节:
无韵无题江南的雨,
渐行渐远塞外的风。
人生失意在天涯,
一程孤旅一程梦。
这里的第一、二行以“江南的雨”和“塞外的风”为核心的意象,对流浪人“一生失意在天涯”的遭际作了背景衬托式的印证。整个这一节则起了一种点化前两节密集的意象表现的作用。从以上两个同题文本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现代歌词《凉州词》的意象是单纯的。由于意念指向明确,使意象组合有机,层次分明;而整体的印证、点化也因明朗、通俗而易于让人接受。虽然这样的意象表现余韵不及新诗《凉州词》,但歌词是无须过多考虑这方面的,因为有音乐可补足。
四、语言策略:直觉隐喻与交流道白
在论述了歌词与徒诗在意象表现上的区别后,我们须明确一点:语言艺术中的意象只能是语言化意象,所以考察了意象表现的区别后紧接而来的就该是歌词与徒诗在语言策略上的区别了。但一谈到诗歌家族中这两个成员的语言,我们也不得不反过来说:歌词与徒诗的语言其实不同程度都属于意象化语言,没有本质上的区分。须要区分清楚的倒是意象化语言不能完全等同于日常交际语言。后者主要的功能是叙述与说明,意象化语言主要的功能却是抒情与表现的,为此也就要求语言是出于直觉的隐喻化语言。这一来,这类语言也就和意象化挂起钩了。须明确如下这点:凡意象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就必然是语言化的。而意象是出自于心物直觉感应的,其功能就是对情思意绪的宽泛式隐喻。因此,所谓的隐喻语言也就是意象化语言。相对于这类语言,日常交际用语只是构成它的物质材料而已,二者在构成策略上是不同的。日常交际用语以尊语法修辞规范为构成策略,而隐喻语言(或者意象化语言)的构成策略则是反语法修辞规范的。明确了这些以后,再回过来看歌词与徒诗的语言,可以说它们的语言策略纵有区别,却不是本质上的。徒诗是一串出于心灵波澜的自我絮语。当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心灵波澜以语言来显示时,这种语言的构成策略势必会和意识层面那种用之于日常交际的逻辑化语言的构成策略——尊语法修辞规范不一致,显示为“诗家语”所特有的、反语法修辞规范的非常态特征,并具现为词性转化、成分残缺、语序颠倒等语言现象,这在常态生活交流中该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所以,在这种策略指引下构成的“诗家语”,新奇而晦涩,但它很适应心灵絮语的特殊状态。因为正是这种心灵絮语本身,只许暗示,无须明言;絮语中显得断断续续、残缺不全、颠三倒四的情况,倒是正常的。这种种导致诗家语貌似晦涩,却具有隐喻性,特显暗示功能。无可否认:歌词语言的构成策略也部分地吸收了诗家语的反语法修辞策略,如李海鹰《弯弯的月亮》里有“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就省去了本是作为修饰成分的“阿娇”后面的名词,句子残缺;孟广德的《我热恋的故乡》中有:“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藏着微荡的希望”,是反修辞规范的——“希望”不可能是实物而让“土地”收藏;高枫的《大中国》的第一句:“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则是谬理判断。恰恰是这样做,使歌词不仅简洁,还特具暗示力。不过从全局看,歌词却是以采用尊语法修辞规范的日常交流用语为主的。这可以理解,因为歌词所要求的是一种广场宣谕式的群体抒情,要达到以呼求应的交流效果,使用的语言也就非得浅显、明确不可了;并且作为意象化语言,歌词的意象既要求单纯、直接,也就会连带制约着语言非得凝练、切实不可。当然,这样的歌词语言由于太直率、浅显,缺乏暗示力和余韵是可以想见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歌词除了依附于音乐,让音乐旋律语言作补足以外,还有着一个重要的借用力量:大力起用姿势语。陆正兰在《歌词学》中认为:“姿势语是一种‘让文字抛开正常意义’的特殊修辞手法”,她还引用布拉克墨尔的说法:“语言中的姿势,是内在的形象化的意义得到向外的戏剧的表现”,故“词语的语音变成姿态语时才最成功”。她还据此作了发挥,提出姿势语是“成为诗歌语言超越自身、趋向音乐性这个理想境界的一种途径”,因此“歌词中才是真正充满了姿势语”(8)的。这些话虽难免有把姿势语提得过高之嫌,不过姿势语的确是使歌词语言寓有内在情态表现力的重要辅助手段。但这里必须分清楚姿势语有两类:一种是钱钟书提出的拟声类声,即词句完全消义化,成为纯然的姿态,如同布拉克墨尔所说:“几乎完全避开了语言的传达功能,从而创造了情绪的等价物。”对此陆正兰这样解释:“也就是几乎完全不‘传达’,跳过了意义,直接指向某种情绪或状态。”(9)另一种是钱钟书提出的拟声达意。在《管锥篇》中他说:“象物之声,而即若传物之意,达意正亦拟声,声意相宣……”(10)这是指词语的语音经特殊组合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调来作深一层的达意,也就是说:这样做既能显示词语本身的语义,又能超越这表层语义而以情意语调而把握到深层次上的意蕴。总之,姿势语提供的是语言策略语调化。正是这种策略作用下的姿势语,使歌词语言既强化了广场宣谕中更广泛的呼应度,也能使呼应关系进入到深层蕴含中。值得指出:由于歌词能有音乐旋律作依傍,故对姿势语的追求特别有利,徒诗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徒诗很少有姿势语的。
值得比较的是臧克家的诗《难民》和潘乃农的歌词《长城谣》。它们都通过难民的流浪生涯来表达国仇家恨加剧的1930年代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心情。《难民》以灰暗的氛围渲染出农民在逃荒路上的情状:“日头堕到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静静的,孤寂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随后又抓住古镇街头飘动的晚炊这个意象,深入挖掘难民的内心世界:“螺丝的炊烟牵动着一声亲热的眼光,/在这群人心上抽出了一个不忍的想象:/‘这时,黄昏正徘徊在古树梢头,/从无烟火的屋顶慢慢地涨大到无边,/接着,阴森的凄凉吞了可怜的故乡。’”这些全是具体而很能显示感兴功能的意象表现,而作为构筑意象的语言,则处处显出了反语法修辞规范的新奇怪异,如“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螺丝的炊烟牵动着一串亲热的眼光”,等等,都如此婉曲、隐晦,联想激活力和暗示性都特强。这种弹性强、密度高、有很强表现力的诗家语在歌词语言中就极少见。《长城谣》里这样写流亡关内的难民情状与内心痛苦:
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挡,
苦难挡,奔他方,骨肉离,父母丧。
这里的意象是类型化的,显出抽象概括以作印证的特点。要说语言的意象化,就很薄弱,纵使也有类型化的意象存在,对构筑它的语言来说,也只能是一种尊语法修辞规范的存在,属于平常人际交流、人人一听就懂的陈述,而无新奇怪异,也谈不上有暗示力。歌词语言这种特点便于让大众接受,适合广场宣谕中的呼应、鼓动、交流,也便于谱曲。却也不能不说它有很大的不足。这种不足如何补足呢?一是依靠音乐旋律,二是大力起用姿势语。其实给这种语言装上音乐旋律的翅膀,能显出分外新异的语调,是最大的姿势语的显示。但这里不谈音乐旋律,暂且搁起。这里只谈歌词语言自身外延的姿势语所能发挥的补足作用。由聂耳作曲的一些歌曲,常常采用姿势语入歌词,使歌词语言特显呼应的力感。如《大路歌》,孙瑜作的歌词,充分运用了劳动号子的拟声:
哼呀咳嗬咳!咳嗬咳!
哼呀嗬咳吭!嗬咳吭!
大家一齐流血汗,嗬嗬咳!
为了活命,哪管日晒筋骨酸,嗬咳吭!
合力拉绳莫偷懒,嗬嗬咳!
团结一心,不怕铁磙重如山,嗬咳吭!
这里有大量拟声类声的劳动号子语词,它们是消义化的,是跳过意义直接指向情绪和状态的一种传达。歌词语言“大家一齐流血汗”也好,“合力拉绳莫偷懒”也好,全是直截了当而浅白的广场呼应式交流,没有诗家语那样的婉曲,所以余韵不多。如果单是这样,这歌词自身的语言无疑是干巴巴的。现在掺入了劳动号子的姿势语,干巴巴的局面就全变了,歌自身的语言有了语调感。这种语调又引发出一种力感,生动多了,再配上音乐旋律,力的语调感就更会显得强烈。聂耳谱曲的一些歌词中,也有起用拟声达意的姿势语掺入歌词语言的,如孙师毅作的歌词《开路先锋》,一开头就是:
轰!轰!轰!哈哈哈哈!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这“轰!轰!轰!”有开山炸石的拟声,又有爆炸的达意;这“哈哈哈哈”有笑的拟声,又有朗笑的达意。这样的姿态语置于歌词正常的语言——“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之前,就使“开路的先锋”这个意象表现得更生动更有豪迈感和生命力感。还有一种拟声达意的姿态语除了以模拟原生态的声,来达意以外,还模拟一种行为状态的节奏来达意。如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第一首《黄河船夫曲》,写黄河上的船夫逆流而上奋力划桨冲过险滩:
咳!划哟!咳!划哟!
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
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
行船好比上火线,
团结一心冲上前!
咳!划哟!咳!划哟!咳哟!划哟!……
划哟!冲上前!咳哟!哈哈哈哈……!
我们看见了河岸,
我们登上了河岸。
这里的第一、二行是叠句,“咳”是用船桨顶住急流的拟声,随之一个“划哟”,就以短促急逼的节奏给人以划过一桨,使逆流而上的船前进一寸这一状态的感觉,两行重叠,则更有奋力顶住急流强上两寸之感。接着第三至六行是两个四顿体、两个三顿体诗行的组合,节奏舒徐,传达出已划过一个险滩、趁势奋进之状。紧接着第九、十行又用了第一、二行的叠句,表明又面临一个险滩,同样传神出以大力顶住急流划出一桨又一桨,使船前进一寸又一寸之状态。第十一行“咳哟!划哟”,用拟声和短促急逼的诗行节奏结合来传神出与急流抗争中划桨极用力的情状,随即是“划哟!冲上前”重叠的两行,拟节奏代声以传神地表达一桨又一桨在险滩上奋力直冲的情状。第十二行一个“咳哟”,拟声拟节奏共同传神出这是逆流冲滩中以全力划出的最关键一桨,于是有了第十三行“哈哈哈哈”,是拟声达意的畅怀大笑情状,从而强化了第十四、五行对终于战胜急流险滩之豪情的传达。
由此看来,现代歌词语言虽不及新诗语言的婉曲含蕴,缺乏弹性与密度,但一当姿态语掺入,强化了歌词语调,以呼求应的歌词语言就大放异彩了。这是新诗语言难以企及的。
五、节奏类型:回旋推进与往复交替
徒诗与歌词由于抒情审美的基点——心灵絮语式的自我独白与广场宣谕式的以呼求应不同,也影响到它们在节奏体式上有所区别。在具体论说这种区别前,有必要提一提节奏与体式的关系和节奏类型的具体内涵。在诗歌家族中徒诗与歌词的节奏和体式是一种主从关系,一般说什么样的节奏类型决定着什么样的体式。诗学理论界喋喋不休的自由体与格律体之争,由于不从节奏类型之不同出发来谈,也就成了永远谈不灵清的空论。那么什么是节奏,又如何分节奏类型呢?所谓节奏,是事物在运动中时间上表现出来的周期性,也可以是事物在静止中空间上表现出来的周期性。作为诗歌家族的两个成员,徒诗与歌词都是吟诵性的艺术,都显示着声音运行中高与低、强与弱、快与慢、对比与重复等变化的周期性规律。但声音运行中高低、强弱、快慢的变化,可以显现为对应等量交替的周期表现,也可以显现为等比递进—递退的周期表现,这就使吟诵艺术的时间节奏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回旋推进类,另一种往复交替类。当然,这两种节奏类型要具体显现还得依赖于节奏基本单位。歌词与徒诗一样,节奏基本单位是音组和由音组组合成的节奏诗行。音组须定量,一般传统汉诗中音组有三个型号来显示它的定量:单字音组、二字音组、三字音组。新诗中增加了一个四字音组。到此为止,不能再增加新型号了,否则就要分裂。音组也须定性,单字音组最舒缓,二字音组次舒缓,三字、四字音组则急促了。音组定量与定性对建立诗行节奏很重要,因为诗行节奏是靠音组组合显示出来的。建行中音组组合也须定量,一般以不超过五个音组组合(即五顿)为宜,否则诗行节奏会十分拖沓沉滞。一个诗行中同一型号的音组不能并置三个以上,否则节奏感要大为削弱。诗行容纳的音组数(顿数)的多寡——也就是说诗行的长度也须定性,一顿体、二顿体诗行急促,三顿、四顿体舒缓,五顿体以上则转为沉滞了。根据这样的节奏基本单位来组行成节,组节成篇,也就会显出回旋推进与往复交替两类节奏表现,与之相应的则是两种体式。而歌词与徒诗——特别是现代歌词与新诗,也就因此而有了体式的区别。
一般说,回旋推进类的节奏表现立足于诗行组合,具现为顿数多寡形成不同长度的诗行在前后顺差组合和两极突兀组合相结合中,以递进—递减反复出现的一种声势语调螺旋般推进的现象。这样的节奏表现以其声势语调之起起伏伏(有时甚至是大起大伏)的周期性运行规律,特别有利于传达心灵絮语式的自我独白。正是这种出于无意识的自我独白,往往表现为个体情绪本然消涨而又潜在地在向前推进的周期,所以这种节奏类型和徒诗——特别是新诗也就一拍即合。由于回旋推进类节奏是长度不同的诗行顺差或突兀组合形成的,也就势必会决定具现其节奏的是自由体式。新诗之所以基本上是自由体的,原因即在此。但往复交替类节奏表现的情况就不同了。这种节奏表现立足于诗行群或诗节组合,具体显示为:在组行成节、组节成篇中,它以同长度诗行或不同长度的对应诗行均齐地组合成节,以这类诗节匀称或对应匀称地组合成章,由此反复展开而造成去而复来、交替有序,声势语调显示为类似原处打转的周期性运行规律。这种节奏表现特别有利于传达广场宣谕式的群体呼应。正是这种出于意识层面的群体呼应往往表现为群体意绪你呼我应、去而复往地在原点不断兜转。所以这种节奏类型同歌词——特别是现代歌词也就一拍即合。往复交替类的节奏既以句群均齐,节间匀称的组合显示出来,也就会决定其具现节奏的是格律体式。现代歌词基本上是格律体的,主要原因也正在此——当然为了便于谱曲而让节奏体式显得琅琅上口,和谐匀称,也是一个原因。
上述的看法,我们可以拿现代诗歌与新诗中一些成功的文本作例证来比较一番。戴望舒曾写过一首著名的新诗《雨巷》,他还因为有这首诗而被誉为“雨巷诗人”。此诗广为流传久而不衰,出生于1960年的刘天华还把它改成歌词而谱曲传唱。但这两个文本在节奏体式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尽管刘天华在歌词改写中尽一切可能地努力于忠实原作,也无济于事。原诗是首参差不齐的自由体,且引其中的前两节:
撑着油纸伞,独自 232 徐缓
彷徨在悠长,悠长 322 徐缓
又寂寥的雨巷, 42 急促 递退
我希望逢着 32 急促 递退
一个丁香一样地 223 徐缓 递进
结着愁怨的姑娘。 232 徐缓 递进
她是有 3 急促
丁香一样的颜色, 232 徐缓 递进
丁香一样的芬芳, 232 徐缓 递进
丁香一样的忧愁, 232 徐缓 递进
在雨中哀怨, 32 急促 递退
哀怨又彷徨。 23 急促 递退
根据上面有关节奏基本单位的论述,我们把这两个诗节的各行标以数字符号,显示它们各自的顿数(即诗行长度),又把诗行顿数相同(即诗行长度相等)的进行归并,以显示三顿体诗行群的徐缓节奏,二顿体和一顿体诗行群的急促节奏,又标明第一节从第一、二行的三顿体起始,第三、四行顺差组接属递退,第五、六行持续顺差组接属递进;第二节从第一行一顿体起,第二、三、四行顺差组接属递进,第五、六行持续顺差组接属递退。由此可以见这两个诗节的节奏进展关系,就诗行顺差组接看是“递退—递进+递进—递退”,即诗行顺差组接使两个诗节各自完成了起伏缓急的节奏周期,但它们的节奏周期就诗行顺差组接运行轨迹看刚巧相反。至于它们的节奏进展,第一节是“徐缓—急促—徐缓”,第二节是“急促—徐缓—急促”,也刚巧相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两个诗节节奏运行周期是改变方向的,这种方向的改变正反映着节与节之间节奏是在回旋中显示着推进。由此窥一斑以知全貌,足以证实《雨巷》不仅以诗行参差也以回旋推进的节奏而显示出与它相应的体式属于自由体。刘天华把这首新诗改成歌词,最显著的变化是在节奏体式上,也引前两节:
独自撑着雨伞 徘徊在悠长的雨巷
多希望遇见一个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有丁香一样的颜色 她有丁香一样的芬芳
她像我一样撑着油纸伞 彷徨在雨巷
忽然一位姑娘 出现在寂寥的雨巷
梦一般凄婉迷茫 有着太息的眼光
她有丁香一样的颜色 她有丁香一样的芬芳
我身旁飘过独自的女郎 走到了竹篱墙
它们就显示为节的匀称,即对应诗行的顿数都是一致的,而两节各自内部一、二、四行都是六顿的,诗行长度均齐,只有第三行都是八顿,两节且是同一个句子的重复,这样做一个目的是既不致使节内诗行长度绝对均齐,也不致使两节所有诗行也绝对一致。正是为了避免造成节奏麻木,才这样稍作变化使节奏进展有了适度的波伏感。另一个目的是通过第三行的这种“出格”行为,把两节的这一行是同一个句子、同一个意思的现实凸现出来,以示这是节内和节间的主旋律。这种种措施都无非是为了声音的运行显出对应等量交替的周期性,从而凸现歌词具有的是一种往复交替的节奏形态和格律化的体式。不妨再拿同写船家女行状的两个文本来作节奏体式的比较。蔡其矫的新诗《船家女儿》写一个“诞生在透明的柔软的水波上”,“发育成长在无遮无盖的最开阔的天空下”的船家女儿,先是一连用了五个四顿体的诗行:“太阳和风给她金色的肌肤,/劳动塑造她健美的形体,/那圆润的双肩从布衣下透露,/那赤裸的双脚如海水般晶莹,/强悍的波涛留住在她眼睛。”这种节奏诗行持续五次的重叠,既有一种舒缓节奏感的高位蓄势,也给人以欲求超越的节奏推进的预期。于是也就进一步出现了如下的诗行:
最灿烂的
是那飞舞着轻发的额头
和放在桨上的手;
当她在笑,
如感到是风在水上跑,
浪在海面跳。
这里共六行,三行一个节奏单元。这两个单元的节奏诗行群都是“一顿体+四顿体+二顿体”,即“142”的组合,从节奏运行来看,都体现为“急缓急”也即“扬抑扬”的周期,两个同一节奏周期的叠合,以高度的跳跃感强化了对此前五行过多迟缓节奏高蓄位的超越,显出了整体节奏运行的推进。这是一首以参差不齐的诗行组合显示回旋推进类节奏特征的自由体诗。而李隽青的歌词《渔家女》,在节奏体式上则是另一番风景:
天上旭日初升,湖面好风和顺,
摇荡着渔船,摇荡着渔船,
做我们的营生。
手把网儿张,眼把鱼儿等,
一家的温饱就靠这早晨。
男的不洗脸,女的不搽粉,
大家各自找前程。
不管是夏是冬,不管是秋是春,
摇荡着渔船,摇荡着渔船,
做我们的营生。
这是“ABBA”式节的组合,相抱的节都是匀称的,其对应的句子也均齐(除二、三节的第三行出格),所以它是很标准的一首具有往复交替节奏形态的歌词,而相应合的是体式属格律体。
现代歌词与新诗在节奏体式上的区别于此可见。
综上所述可见:歌词与徒诗——特别是现代歌词与新诗,的确明显地存在着区别。这些全是因抒情审美基点的差异导致的。唯其如此,我们在结束处才还得强调地提出:这种区别并不属于质的规定性。从本质上说,歌词与徒诗都是诗歌家族的成员,都是语言艺术的,尤其都属抒情的语言艺术,只不过抒情的出发点与传达的角度不同,才派生出它们之间的种种区别。澄清这一点非常有必要,因为现代歌词与新诗似乎距离在越拉越远,歌词研究界也在过分强调歌词对音乐的依附性。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只希望我们的这场“区别论”不至于助长这种不正常。
注释:
陆正兰:《歌词学》,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同(1)。
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绿原文集》第3卷,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同(1),第119页。
王克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同(6),第174页。
同(1),第88-89页。
同(1),第91页。 钱钟书:《管锥篇》,《钱钟书文集》第1册上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