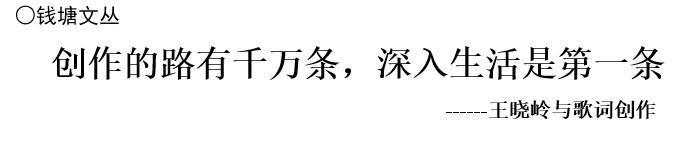繁荣在文学边陲的歌词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歌词作品开始闯进了文学视野。这体现在进入新时期的三十多年来,中国作家协会中的歌词作家会员持续增加。同时,从1994年起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新诗研究所在所编印的《中国诗歌年鉴》中,坚持收入一定数量的当年产生的优秀歌词,从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1999年,在继谢冕先生编篡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诗歌卷)中收入了乔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与崔健的《一无所有》等三首歌词作品之后,《诗刊》也于同年7月号推出了“乘着歌声的翅膀”歌词小辑,除发表了“乔羽答主持人问”的关于诗与歌词的访谈文章外,还选发了20位作者的30余首歌词新作。之后,由中国新诗研究所编选、重庆出版社出版的3卷本大型巨著《新中国50年诗选》中,又破天荒地在专门开辟的“歌诗篇”内,一举收入了当代69位作者的79首歌词作品。对于歌词艺术来说,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值得惊呼的创举。
一、
歌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兴起的一种语言艺术,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发挥着自己几乎是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当我们从小说、戏剧、纪实文学、诗歌、美术等作品中不时能够发现某些时代本质方面的时候,同样也能够从歌曲中聆听到当时时代的一些最强音,而歌曲那种强烈的震撼力又往往来自于歌词,问世于1935年、今天仍然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也许正是这一点,现代文学史中不少诗人们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数量不等地留下了自己的歌声。
作为语言艺术的歌词,固然应当是一种韵文文学,但因为它的创作是完全为着与音乐旋律的结合而设置的,故其文学色彩便因为不能不受到音乐的严格约束而有所减弱、有所散失。应当说,音乐对歌词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歌词文学性的一种限制,而唯其限制,才使得歌词有时能够产生令人拍案叫绝的佳句或佳作,但更多的时候,歌词的文学色彩则难以同纯文学作品相比,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也因为此,黑格尔则索性断言,歌词往往只是诗人作品中那些“中等的诗”;我国现代作曲家、语言学家赵元任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诗唱成歌就得牺牲掉它的一部分的本味,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他们对歌词本质的这些论断,无疑中肯而精当。
然而,歌词正是因为存在着与音乐这种最具恒久性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可能,故某一首歌词一俟获得了恰到好处的机缘,成为了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晓甚至所喜爱的歌曲后,其影响的广泛、传播的持久却是任何其它艺术形式所难以比拟的。而此类实例从昨天到今天确乎是屡见不鲜。君不见,一些诗人与作家在某个历史阶段的歌词作品,一经谱曲传唱后,其知名度与影响力往往会远远超过其它影响颇大的诗歌作品,以如《义勇军进行曲》之于田汉,《黄河大合唱》之于光未然,《二月里来》之于塞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之于公木,《南泥湾》之于贺敬之等等,都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到了今天,同新诗相比,歌词领域则显得更加红火热闹一些。这正如乔羽同志所说,歌词“由于有影视、舞厅等现代传媒、又明白易记能唱,形成了一条群众性的宽阔的长河。”这,恐怕正是歌词艺术具有与音乐结合后得以走向广大群众之中所形成的的最大优势所在。
二、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途程中的客观原因,使得歌词艺术同许多姊妹艺术相比,显得实在过分年轻而稚嫩了一些,也使得我们的歌词作者队伍只是在极其短暂的几十年时间里,便经历了一个我国百余年近现代歌词史上前所未有的迅猛壮大的过程,更使得我们的歌词作品所应当经历的逐渐走向繁盛的过程,不能不显示出有几分匆忙。
姑且不论战争年代的情况,仅以新中国成立之初而论,当时我们的专业歌词创作队伍还未曾真正形成阵容的五、六十年代的那段岁月里,除了从战争中走来的一批部队文艺团体的文艺工作者之外,相当一部分歌词作品则出自一批当时蜚声文坛的诗人们的笔下。郭沫若、光未然、郭小川、贺敬之、公木、管桦、袁水拍、袁鹰、邹荻帆、张志民……一个时期里,他们的名字无不与歌词、歌曲发生着无从解脱的联系。
诗人们创作歌词,虽然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然而歌词既然是与音乐结合的一门艺术,它也应当形成自己的一支创作大军,这也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无论专业与业余的歌词创作队伍,都还没有能够真正形成蔚为壮观的喜人势头。没有自己的队伍,便不可能产生自己的刊物,更不可能有自己的组织诞生――尽管那时的一些逐渐萌生着的业余作者以极高的热情,将自己的作品不断寄给各种音乐刊物编印的以油印方式问世的内部歌词资料,以求谱曲面世;尽管那个时期里,一批优秀的歌词,像郭沫若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沙鸥的《我们快乐地歌唱》,袁水拍的《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光未然的《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管桦的《快乐的节日》、《我们的田野》,乔羽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祖国颂》,艾青的《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公木的《英雄赞歌》,李鉴尧的《马儿啊,你慢些走》,袁鹰的《军垦战歌》,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张永枚的《骑马挎枪走天下》,阎肃的《我爱祖国的蓝天》,敏歧的《拉骆驼的黑小伙》等等,由于同音乐的比较完美的结合并经过歌唱家们的演唱后产生了极佳的社会效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这种歌词艺术在那时还只能生存于音乐的羽翼之下的现实,却是无可改变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十七年里,歌词作为一个具有文学与音乐双重品质的艺术品种,不仅没有一个作者出版过自己的歌词专集,连多名作者的合集也是因为任务的所迫,只仅仅由当时的音乐出版社出版过只有一两个印张的薄薄的《万里长江笫一桥》等两种。至于出版发表歌词的刊物与建立歌词作者的组织,更是痴人说梦。实在地说,那个时期里,与诗人、作家们相比,歌词作者们连获得“歌词作家”的称谓也未能成为事实,更不用谈及其它了。
三、
歌词艺术的长足发展与突飞猛进,是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之后。也许是由于十年“文革”时期里,除了“语录歌”与“红太阳”颂歌之外,歌曲领域里留下了大片的洪荒的客观现实,意味着亿万人民对于歌曲艺术的需求处于一种饥肠辘辘的状态中,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它所提供给歌词作者们的创作机遇,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国门的打开,使香港、台湾以及西方歌曲文化构成了一种无可抵挡的巨大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千百万人民的文化生活领地。于是,当十七年里所产生的一些歌曲作品在一个短暂时间里满足了人们某种怀旧心里之后,不断创作全新的、并且是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甚至不同流派的歌曲新作,便成为每一位对歌词、歌曲创作怀有浓厚兴趣的人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于是,人们看到,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为了歌曲的真正繁荣而应运而生的各地歌词作者队伍有如雨后春笋拱土而出,各种内部的歌词报、刊在比十七年里更大的层面上纷纷面世,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讲习班也在各地不断举行,而我国现代史上笫一份专门刊发歌词的专业刊物――《词刊》也于1981年正式创刊;五年之后,我国现代史上笫一个歌词作家的组织――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亦宣告成立。这一切,无不是一种信号,一种标志,而它们相继诞生的坚实基础,无疑是歌词创作本身的繁盛与兴旺。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来,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从没有一个时期的歌词艺术会像今天这样呈现出如此万木争荣、万花竞艳的局面,从没有一个时期歌词艺术会受到人们如此普遍而热情的关注,也从没有一个时期会有这么众多的人们如此饶有兴趣地跻身于歌词创作的行列里。
的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相继涌现出来的许多优秀歌词作品,以其无可争议的创造性的实绩,证实了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乔羽的《思念》、《难忘今宵》、《说聊斋》,阎肃的《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雾里看花》,张藜的《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山不转水转》,晓光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就是我》、《光荣与梦想》,王健的《歌声与微笑》、《绿叶对根的情意》,石祥的《十五的月亮》、《望星空》,郑南的《请到天涯海角来》、《大地飞歌》,陈哲的《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陈哲、小林、王健等的《让世界充满爱》,李幼容的《金梭与银梭》,陈小奇的《涛声依旧》、《烟花三月》,瞿琮的《我爱你,中国》、《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王晓岭的《祖国赞美诗》、《风雨兼程》,石顺义的《黄河源头》、《白发亲娘》,凯传的《高天上流云》,任志萍的《心愿》,易茗的《好人一生平安》,邹友开的《好大一棵树》,任卫新的《我们是朋友》、《走到一起来》,韩伟的《祝酒歌》,贺东久的《不要问为什么》,马金星的《军港之夜》,陈克正的《再见吧,妈妈》、甲丁的《我们告诉世界》,崔健的《一无所有》,黄小茂的《懂你》宋小明的《你是这样的人》等等等等,已经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光耀日月的歌词艺术长廊。
四、
在歌曲中,音乐艺术的形象并非音乐自身所固有的,而要靠语言与欣赏者的联想才能完成。正是从这个特点出发,歌词在歌曲中的地位与作用才举足轻重,这一点恰恰对歌词作品的艺术水准提出了无可忽视的要求。
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在十七年还未曾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的情况下,又经过十年浩劫的停滞与封闭,在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的新旧交替时期里歌词的突然迅猛发展,必然会是一个大潮汇流、气势汹涌的景观,这种景观既产生气象万千的无限风采,也会伴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遗憾。于是人们看到,近些年里的歌词创作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生产领地,以电视(文艺晚会、音乐电视、电视剧)、音像出版(盒带、CD、VCD)等多种手段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以往出版发表与广播、电影的单一化生产方式。而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与手机传媒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促使歌曲的生产与传播方式进一步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局面,也使得以前相对比较稳定的专业与业余歌词作者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八十年代前的专业与业余两支队伍重组为今天的四支队伍,即服务于部队与地方政府所属表演团体的专业作者、从业于音乐文化市场的职业音乐人、专事网络歌曲创作的业余作者和依旧以纸质传媒为展示作品成果的业余作者。而这种变化的根本特点又使歌词创作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而多渠道的问世方式必然使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纯粹的娱乐化与流行化倾向对于歌曲持久艺术生命力的挑战,就是突出的一点。
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进步,是一种繁荣。然而,由于歌词艺术自身历史的短暂,歌词队伍相对的年轻,在这种形势面前就空前显示出了其由于准备不够、仓促上阵所带来的一些不足。比如,有的作者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依然沿袭以往的“工具意识”,一味追求题材大、口气大、口号响,致使作品语词落套,内容空泛;有的因确乏应有的人文关怀与深厚的生命体验,使得作品往往只能就事论事、平淡无味;再如,因语文基础薄弱而导致歌词中的用辞不当、语病迭出,不知所云,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等等;至于一些歌词躲避崇高、回避思想、一味追求个人化与自我化,却并不付出真情实感因而显得苍白浮泛等等,在一些歌曲与歌词中更是屡见不鲜。而所有这些,无不使歌词招致到来自文学界、艺术界、语文教肓界以至整个社会的种种微词与非议。无疑,歌词队伍的庞大而芜杂、歌词作者的功底不厚、修养欠佳等等,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毋庸置疑的客观原因。
五、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于歌词艺术发展所具有的非同小可的作用,以乔羽同志为首的中国音乐文学学会近些年来才一再强调对歌词理论的系统研究,并以图通过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达到提高整个歌词队伍素质的目的。于是,一方面不断促成了以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为主办方的一些当代歌词作家与作品研讨会的相继举办,另一方面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曾组织力量对歌词概论、歌词美学、歌词史、歌词创作、歌词作家、歌词作品选等领域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以几位任职于高校的中青年学者为主力军的努力下,十多年来,陆续出现了一批令人喜悦的理论研究书籍。主要有《歌词创作美学》(许自强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中国当代歌词史》(晨枫著,漓江出版社,2002),《现代歌词文体学》(苗菁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音乐文学概论》(庄捃华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歌词门》(王晓岭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歌词学》(陆正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中国歌词流变概观1900—1976》(苗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歌词创作的原理和方法》(毛翰著,线装书局,2008),《百年中国歌词博览》(上、中、下卷,金波名誉主编,晨枫主编,苗菁、毛翰、傅宗洪选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歌词美学》(魏德泮著,作家出版社)等等。这些蔚为壮观的理论研究成果,既昭示着歌词艺术理论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有志者们的关注,开始从白手起家实现了业绩初现,也必然会给歌词的进一步走向更大的繁荣,起到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在文学视野边陲不断繁荣着的当代歌词,用自己艰辛而又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跃入了自己历史发展征途上的重要时期。今天,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刻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成果,不断证明自己的真实价值,给我们伟大的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留一份更加珍贵的精神财富,才恐怕是每一位歌词作者都应当真诚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