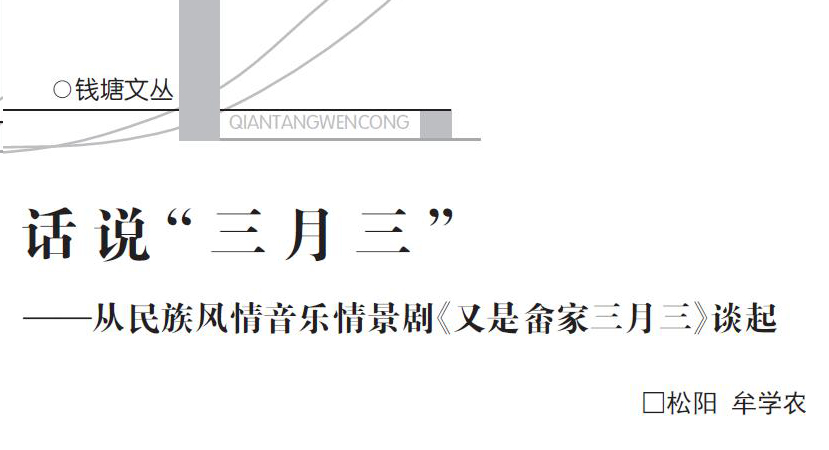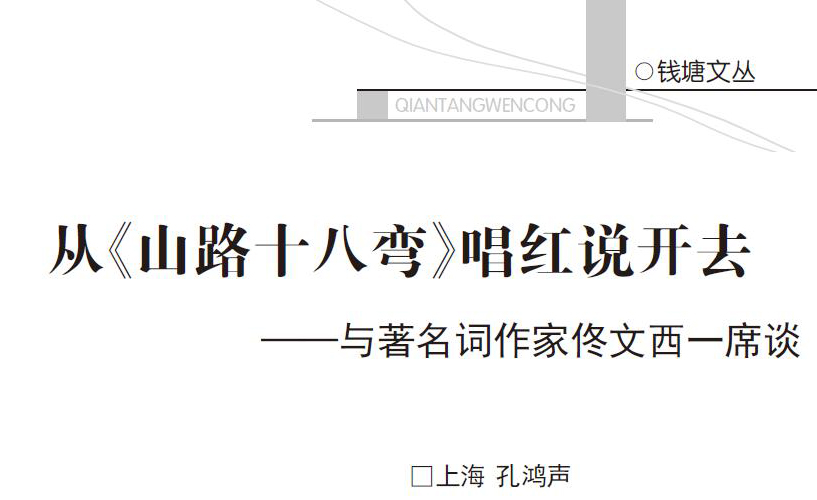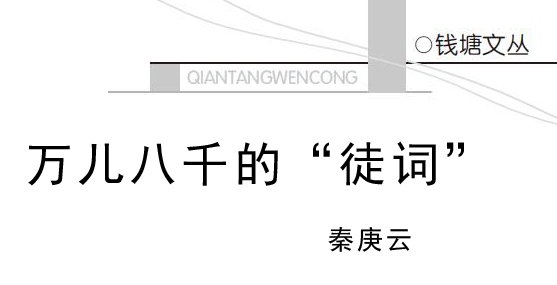到底是谁的歌?

作者赘言:下面的这篇文稿,是将近两年前完稿的。旨在对于出现在某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欣赏歌曲名作时只谈演唱者而对于曲作者却只字不提的做法,提出了异议。但文稿写成后没有适合的机会,也就一直搁置在电脑里。
无独有偶。近日,在翻阅《花港词刊》2013年第4期时,又读到一篇类似的文章。作者在对广州军区歌词名家陈道斌的作词歌曲作品进行品评时,依旧是只提演唱者,对于所有曲作者同样是只字未提,这就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篇被压在文件夹里的文稿来。
我以为,歌词评论者如果只是对于歌词作者的文本歌词(亦称徒词,即未曾谱曲成歌的纯文字歌词)进行赏析时,就歌词谈歌词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但如果是对作者被谱曲并演唱后成为歌曲中的歌词进行评论、且文中既有作词、更有演唱者而唯独省略了曲作者现象的出现,恐怕就有悖情理了。
作为歌词作者的我们,谁都不会不明白,词、曲作者都属于同一首歌曲的一度创作者,也是该作品的著作权共同拥有者,两者在相辅相成中因歌曲而融为一体。但当我们在评论某首已经作为被演唱、甚至已经广为人知的歌曲中的歌词时,为什么参与这首歌曲演绎的二度创作的演唱者总是会被醒目地凸现了出来,而一度创作的另一半——曲作者的名字却被莫名其妙地抹去了?
据此,我又联想起其它类似的现象来:比如,我们的一些作者在介绍自己的“歌词代表作”时,
这种一首歌曲只知谁唱的而不知、也不问谁写的现象,如果发生在普通大众身上,无疑司空见惯,似也合乎情理,但出现在歌曲作品的歌词作者中,恐怕就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了——这究竟是因为忘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某某歌唱家演唱的某某歌曲,但曲作者照例被悄然地省略而去。其实,也是同一种思维意识的反映。记?还是由于疏忽?或者是……
这种现象的不断出现,让我不能不联想到一个尖锐的问题来,即:歌,到底是谁的歌?仅仅是演唱着或者只是歌词作者的吗?而此种疏忽如果继续蔓延下去,就连我们歌词作者自己的名字也会被忘记和被疏忽的。这绝非耸人听闻!如若不信,读读下面的这篇经过我略加修订的旧文稿,就会看到真切的实例。
究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不想在此详加分析。但只想指出,这既与我们庞大的文本歌词作者群体的存在现实有关,也同我们相当一部分歌词作者长期惯于疏离音乐有关,更同我们的歌曲艺术生产的方式有关,还同我们的歌曲艺术市场化运作的深度有关。
是否如此?我期待诸位词门众生以至音乐同仁们一起探讨、共同商榷。
偶尔在某刊物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在长达4000余言的行文中,满腔热情地列举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旋律“在你血管里激荡”的歌曲名作,并一首一首进行了分析。应当说,这样从关照与回顾历史中获得有益的思考,无论是对于歌曲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是值得珍视的。
然而,读完文章,我却并未能被作者的激情所感染,反而有一种无法排遣的失落感久久压在心头,总也挥之不去。这是因为在作者所列举的9首歌曲中,除了《让我们荡起双桨》与 《月光下的凤尾竹》分别写明“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与“施光南作曲、倪维德作词”之外,另有一首《飞吧!鸽子》,虽注明是“王立平作词作曲”,但却分明是错将词作者洪源先生的署名权莫名其妙地馈赠给了王立平先生。
如果说这种张冠李戴还有情可原的话,那末文章作者对于所余6首歌曲则是一律只提演唱者,而将歌曲的词曲作者一律抛却脑后,只字不提。这样的做法令人实在难以接受。
请看事实:
“王洁实和谢莉斯演唱的《校园的早晨》,在那个年代可以说风靡一时。”这里,词、曲作者高枫与谷建芬的名字却被糊里糊涂地省略了;
“张振富和耿莲凤演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真正唱出了青春飞扬的自信、活力与豪迈!”同样,词、曲作者张枚同与谷建芬的署名权也被莫名其妙地剥夺了;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那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如清泉奔涌,”照例,动人的歌词被引用了,歌名《假如你要认识我》连同词、曲作者汤昭智、施光南却被无缘无故地埋没了;
“如果让全国人民投票推选,我想歌唱家彭丽媛演绎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高居榜首。”这首几乎记载着一个伟大变革时代最强音的歌曲作品,其词、曲作者晓光与施光南的名字照旧未见踪影;
再看,曾经唱响两岸四地的《我的中国心》,除了指明是被“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将一位香港演员请上春晚舞台”的张明敏所演唱之外,香港歌词大家黄霑与作曲家王福龄,也遭到了对其署名权不予理会的结果;
其余像被称为“妩媚温婉”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的台湾词作者丁晓雯、曲作者K/Halonen以及被誉为“清新典雅”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的台湾词作者李子恒、吴若权与曲作者李子恒,其署名都一律被湮没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众所周知,由于歌曲艺术的特殊性,歌曲创作的词曲作者作为一度创作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恰恰是完成了一种艰苦的、完全独创性的精神劳动与心智付出,完成了一种不可模仿也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自我创造,因而,他们享有的著作权、包括署名权,也理所当然应当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护。这一点,在我国和世界各国的音乐著作权法中都毫无例外地获得了申明。与此同时,演唱者的演唱,则是在作者创造成果基础上进行的演绎,属于二度创作,这种演绎无法改变更无法取代作者所拥有的原创性本质。但兴许是缘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原因,往往提起某首作品,只知道是某某歌手演唱的,其作者却不为人所知。这种现象意味着作者的署名权也无形中被剥夺了,而作者的署名权又是著作权人最起码的一种基本权益,具有不可侵犯的专属性。这里,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普通听众身上,那也无可指责,而出现在身在这个领域、又在对歌曲艺术进行研究、评介的文章或著作中,或者是公开发表在公开出刊的刊物上,其对作者所应享有的著作权与署名权的漠视,实质上是反映了作者对著作权中有关作者权益有关条款的置若罔闻,这是万万不能予以宽谅的。
实际上,作为一名歌词作者的此文作者,其在文章中所列举的曲目均属名作,对它们的作者本来应当知晓,并有责任一一注明。即使个别不知道的,在行文时至少也应当认真查找,此乃举手之劳,并非难事。但问题还是出现了。这里,我们先暂且避开法制意识的话题,我只想说此事所反映出来的,实属当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浮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也证明了我们的作者头脑中缺乏一种对于精神产品的创造者的尊重与敬畏之心,更显露出我们的歌词从业者只管埋头去写、只求发表而从不注意学习和充实自己的短视心理。这里,我想顺便问问文章的作者,如果某一日,你的歌词被谱曲、演唱后走红四方了,别人在品评这首歌曲时,只是对于演唱者进行了多方褒扬,而对作者只字未提,你将作何感想?你的内心又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在此,我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另一件事情——某家歌词刊物的编辑在赴某地开会时,见到了当今的某省音乐文学学会的会长、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曾经写出过唱响一时的作词歌曲名作的词作家。按说,不论是作者还是编辑,只要身在当今歌词界,不应当对这位词家有所不知。反而论之,即使是以往不知,此次这位编辑同这位词家同一起开会甚至还同台领奖,总该相识了吧!但事实并非如此:君不见,这位编辑在会后所写的会议综述文稿中与所发出的的照片中,竟把这位词家所在的省份来了个张冠李戴,又硬是将他的大名白白写错,且错得离奇古怪。此事所证明的正是,这位编辑与这位词家真的是陌路相逢、并不相识。
这件不该发生的失常事件,在令人感到可笑的同时,更加感到可悲。而其后面所隐藏的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只去责怪这位编辑一个人,显然是不公允的,我在想,至少此次活动的主办方也同样难逃其责。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我们有的作者和编辑们,平时只知一味追寻一歌唱红天下的梦想或者只图关注自己的作品效应,大约很少能够静下心来去关注前人,学习他人,也就更谈不上去借鉴台湾、香港以及国外的作家作品了。否则,是不会闹出自连己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也是半明半暗、懵懵懂懂的笑话来的。
于是,我在想,也许只有那些懂得敬畏生命、尊重他人,真重他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并不断从中充实自我的人,才可能最终成就自己。
※ 此文标题源自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正兰女士的新著《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第223页中的一个命题,特此说明并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