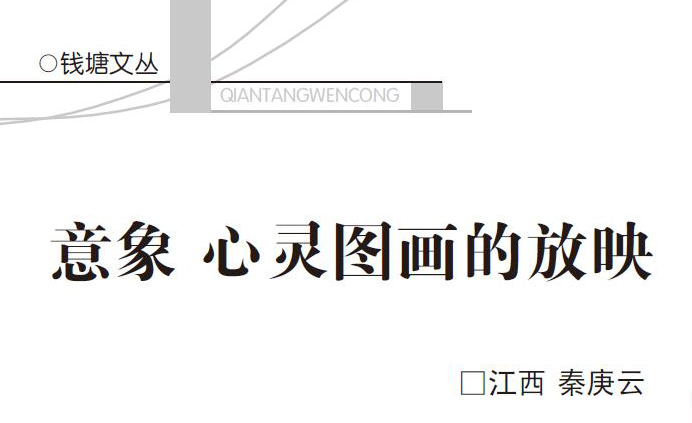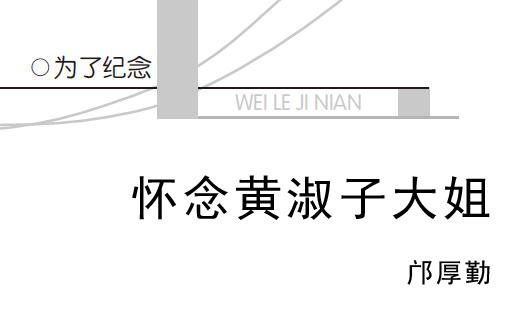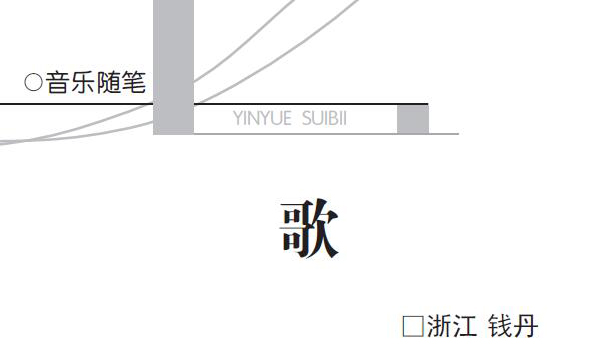从黑夜一直唱到天亮

一
周云蓬以一组《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获2011年度《人民文学》诗歌奖,让人有些意外。近年的《人民文学》多次发过歌词,大多为摇滚、民谣、说唱类风格的作品,有些词作者本身就是独立音乐人、酒吧驻唱或民谣歌手,除周云蓬外,有宋雨喆、万晓利、小河、刘东明、张玮玮、钟立风及“野孩子”张佺,写过《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的邵夷贝,“幸福大街”主唱、侗族清华女生吴虹飞等。在诗界对歌词不屑的气氛里,这家国内最权威的文学刊物执意发点歌词,并正儿八经发一块有文学质地的奖牌,虽有点试水意味, 却足见一个大刊的气度、识见与良善。
据诗歌编辑朱零透露,周云蓬缘于评论家李敬泽的推荐,他说听了周的歌后有一种冲动,一些句子“打动了他坚硬的内心”。后来,朱零在《读诗札记》中提到:“我至少认真看了四遍周云蓬的歌词,这些歌词确实有股清新之气,比起“老婆老婆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之类听着就起鸡皮疙瘩的流行歌曲,不知要强上多少倍”。
在流行乐坛,民谣带着拱出泥土的青湿之气,一直旺盛地长着,尤其在年轻人聚集之处,先锋的、乡土的、反叛的、俚俗市井的、小可爱小清新的、小资怀旧的、甚至荒诞怪异的……… 几乎什么流派与风格都有。周云蓬与小河、李志、左小诅咒、张佺、朱芳琼等一拨人,可谓是“诗性民谣”的代表,他以“唱与作”为自己挣得了荣誉,人们称他为“当下中国最具人文色彩的民谣歌手”。 2008年,还获了圈内颇受好评的第八届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及“最佳作词人”奖。他的创作涉及诗歌、散文、随笔,成了韩寒《独唱团》杂志的开篇作者,分别在台湾与内地出版了《春天责备》诗文集。
1970年出生于辽宁的周云蓬,9岁时失明,15岁弹吉他,1994年毕业于吉林长春大学中文专业,21岁写诗,24岁开始“在路上”漂泊,2003年,他签约摩登天空旗下的Badhead后,是命运转折的开始,在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中,精美、细致的编曲和充满人文色彩的歌词,浑厚的磁性嗓音,喃喃自语地描绘着一幅幅宁静、古朴的生活画面,旋律中流着哲理、感伤及发乎于心的真诚。之后,又出版了《春天责备》、《中国孩子》、《清炒苦瓜》、《牛羊下山》、《红色推土机》等专辑。风格嬗变,除吟唱爱情及个人痕迹深重的生命状态外,歌词的内在意义强化,社会指向与时代性大为增强。
二
行走与停留,都与生命节奏有关。如果给2010年后的周云蓬描像,不应忽略那一顶乌毡帽。这年春天,周云蓬终于落脚在绍兴戒珠寺西街的一条巷子里,这条受保护的老街,外人问起时,当地人总会加上一句:“那是王羲之住的地方”。
且歌且行的他有些疲惫了,游唱到了杭州,但因为杭州的房租太高,加上南方的闷热,最后只得考虑租住在离杭州不远的水乡城市绍兴。他说:绍兴的鲁迅、蔡元培都是他喜欢的文人,比起北京,这里空气好,物价低,离他心仪的杭州也很近。他厌倦了到处搬家的生活,面对不访自来的细雨敲窗,在看不见纷扰的尘世间,听屋檐下的流水,闻空气中飘散的黄酒味道,有清秀、好性情的女友伴在身边,而此地的民风也像老酒一样纯正,生活中似乎有一种醇厚的清香。此后较长的一段日子里,他一般是上午睡觉,临中午时读书、写作,下午四时以后由女友绿妖牵着,乘公交车赶往杭州,一直唱到深夜,再乘火车回到绍兴。绿妖的手,是他日常生活中的眼、光芒与道路。
高个、墨镜、胡须及一头中长头发的周云蓬,固定的演出形象多了一顶帽子。有人问老周那顶黑色斗笠是什么?像电影《佐罗》中的骑行侠客,其实它是绍兴特产—-乌毡帽。黑黑的瓦楞般厚实,可挡雨,可防寒,鲁迅先生有诗言:“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就像是穿越了一把时光,他愰忽进入大师笔下江南水镇的场景。
只有手抚一把吉他时,才仿佛找到生命的意义,酒吧营造的气氛让他安静。被黑暗蒙住的他,一支接一支“讲述”生活中发生的故事,掀起的喝彩声、昏暗的灯光、泛起的啤酒泡沫似乎都与他无关。他孤独而自由,生与死、爱与恨、希望与失望,理解与决绝,以歌唱的方式与世界对话交流。
“睁开眼睛就亮天,闭上眼睛就黑天”。“太阳出来,为了生活出去,太阳落了,为了爱情回去;” 对于视障的他,有永远的黑夜在陪伴,他的存在就是要努力掀开蒙住生命的这道帘,与无处不在的黑暗抗争,寻求自身的超越。因而在他的歌中,寄寓了更多的渴望,以及与这个世界纠缠不清的恩怨与眷念。
他一路“讲述”着,既是生存的需要,以保持最低姿态的体面生活,更是内心倾吐的需要,为一直耿耿于怀的艺术,如果丢掉了音乐,也许他的生命真的就黑暗无边了。正如他本人说的:“因为如此,我将自己的颠沛经历化为了歌词,那些歌曲都是饱经沧桑的音符,都是在无数次跌倒后重又拾起,放在口袋里的歌谣。”的确,他的不少词作有着沧桑的部分、哲学的意味,犹如他本人爱读的中国诗歌,还有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加缪《局外人》之类的作品,渐渐滋养成为作品的血液或骨肉,既有感性的倾诉,亦有理性的潜隐,在看似安静的叙述中,文字里藏着波澜起伏的情感,试读《荡荡悠悠》:
我是一个离开了家门,
没有工作的人,
漫无目的的四处飘荡,
寻找奇迹的人。
我也渴望着一种幸福名字叫作婚姻;
我也渴望着一种温馨名字叫作爱人。
我的家里还有个母亲,
她时时为我担心,
为了她我还有一点怕死,
不敢让她伤心。
哦,有所牵挂的人,
哦,无处抛锚的心。
无论天上,无论天下,唯有我独尊,
飘飘忽忽,荡荡悠悠,只有我一人;
一路高歌,一路哭笑,天涯有余音。
从平常不过的口语开始,写着写着,有了微妙的深入,到副歌部分已是诗意升腾,直捣人心了;哭着笑着去天涯追寻,且不敢让老母亲牵挂和伤心。令人想起他的另一首诗《母亲节》:“你生了个黑暗儿子,把他养活成亮堂堂的希望”。这个粗犷又温厚的男人在表达内心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坚硬的背影。另一首《吹不散的烟》,写的是震后的哀伤思念,极冷静的手法,吸纳了一切苍凉,让一种很有力量的东西把刺骨的悲气抑制住,之后往开阔的地方走去,歌唱便有了一种安魂的包容。
汶川,汶川
你在哪里,在天上吗?
我的婆婆
在虚空里做了一碗担担面
那天空镀了金
让人们都看不清
有谁能够扶起一所房子呢?
人说,今年的汶川
满山的樱桃都熟了
已没有人来收割它
一阵烟,化成了云烟
像山一样凝固在我们的头上
不管长年的北风还是来自海上的南风
都不能把他们吹散
请你, 勤劳的土地
请你不要再五谷丰登
因为土地上已没有了他们
在真正的民间音乐中,爱情是其中动人心魄的部分,情歌最怕流于空泛,它有扎实的根。作为民谣歌手的他,既在已逝传统中寻源,又不忘注入时代元素。他认为,对爱情的越是回避,越说明这是一个虚伪、脆弱与苍白的时代。他用自己的方式唱出带有“周氏”标签的爱情。《牛羊下山》专辑中,一首《不会说话的爱情》具有代表性:
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没有窗亮着灯 没有人在途中
我们的木床唱起歌儿 说幸福它走了
我最亲爱的妹呀
我最亲爱的姐呀
我最可怜的皇后
我屋旁的小白菜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境里
虚幻的徘徊
徘徊在你的未来
徘徊在我的未来
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 冒着热气期待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绣花绣得累了吧,牛羊也下山喽”;这是一个多么诗意盎然的年代。然而,幸福总是如此短暂,它在严峻的现实中不堪一击,“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情绪在高潮处突然断裂,转成一场唏嘘谢幕。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周云蓬的细腻,在西藏云游时他出现了高原反应,便在那曲下了车,之后的几天结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给周云蓬找了一家酒吧,他成了那里惟一的汉族歌手。上面唱,下面唤,还要喊他唱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林志炫的《单身情歌》等等。归途中,他把卓玛的电话号码弄丢了,从此失去了联系,但卓玛永远留在他名为《今夜》的一首诗里了:“我想起卓玛,那曲的草原宾馆,有牛粪的香气,今夜你在何方?想起你的笑容,昨天它锁在门外,是否你还记得我……”
据说就是那次西行之后,他在录制完《牛羊下山》后离开京城,携心爱的女友迁往心仪已久的江南水乡——绍兴。
三
2007年5月,周云蓬出版了新专辑《中国孩子》,收入他作词作曲的9首作品。有评论说,这是一张可以与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相媲美的民谣杰作。著名乐评人李皖称“《中国孩子》从房价、黄金周、关于城市的新闻报道、小时候的共产主义之梦获取题材,以从低沉到尖锐、从死寂到呼喝的方式演唱,形同太平盛世的一声晴天霹雳。”
该专辑的引人注目之处,是离开灿烂的街市进入幽暗的小道,那里有人们刻意回避的冷酷的风景,与主流媒体渲染的盛世景象毫不搭调。当电视晚会“嗨”着好日子、唱着幸福欢歌般喜洋洋生活时,他的那些从尘世中挣扎出来的悲凉音调,在酒吧一角肆意生长,说严肃也好,说病态也好,说反讽也好,说偏激也好,一个盲人歌手用不再掩藏的内心声音,直陈现实世界中的痛与黑,让习惯于歌舞升平的人们有些不适应。请读以下歌词:
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
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
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客吃饭了,
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
从今天以后,我要去上班了
我要努力地还钱,我要还清贷款,
不管风雨雷电,我要去上班,
不管天塌地陷,我要去上班
不管洪水滔天,我要去上班,
管海枯石烂,我还是要上班,
我努力地还,我拼命地还,
我要一直还钱,我要还清这贷款,
直到有一天,所有的钱都还完了,
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
——见《房子》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变成了一筐煤
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见《中国孩子》
他把民生的种种酸楚写进歌里,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让人们听见与社会不和谐的摩擦音。在这些歌词中,他减少了隐喻和修辞,认为“事件本身已经足够”。《买房子》唱的是我要一直不停地还钱,直到有一天所有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黄金粥》唱的是极具特色的黄金周,满地黄金,人手一碗粥。最耀眼的是《中国孩子》,把新闻里的真实事件串连在一起,取一个让人揪心的醒目歌名,简直是给一个伟大的国家抹黑?此类沉重的吟唱,让周云蓬如那个拆穿皇帝新装谎言的孩子,说出了藏掖在这个“最好”时代背后的那些“最坏”图景。
也许引发周云蓬痛感的,不是身体的残疾,而是这个世界的病态与残疾。写下这类民谣,不仅仅是勇气,也有一种责任,还有一种更大的关怀,是他作为一个公民的发言。歌以载道,以此方式留下注脚,让人感受到一个盲人歌者内心广阔的世界。他创作的边界不断延展,如写林昭的《四月挽歌》,写汶川地震《吹不散的烟》(曲选用了迈克•杰克逊的《heal the world》),写实验气息浓重的《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还有那首为海子诗歌《九月》的作曲,在高悬的千年明月下,马头琴呜咽,只身打马走过草原,旷世的孤独不可言说,“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似乎已预示了海子此后为自己选择的命运。周云蓬,一个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比我们看到了更多荒诞与多舛的生存,也比我们感受到了更多微弱与耀眼的善美,他以强者的心态吞咽着苦难、参透生命的力量,为热爱的音乐加冕。
周云蓬曾说“人不可能永远愤怒,本质上我不是个性格暴躁的人,写《中国孩子》那时候也是就事论事。”可以说,他的创作是诚恳的,有节制、有选择的,没有必要像某些人那样不安或类似“抗议歌手”的无端阐释。细听之下,在那些本应严肃或沉重的主题下,他依然保持了特有的乐观精神,他调侃黄金周和高房价,开涮自己失明、落魄而又快乐的生活……;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有包容自由思想的胸襟与宽容异声的自信。相反,如果歌坛只是沉浸在一片赞美、甜腻的浅吟低唱之中,反倒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因为这远不是事实本身,也阉割了艺术深刻的灵魂。有人说“好歌词在摇滚中”,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在崔健、张楚、汪峰、许魏、周云蓬的一些作品中,你会找到一种疼的感觉、爱的艰辛、搏击的力量,它与人们真实的生命体验有关。
央视的文化栏目主持,“火柴的火,安静的静”曾对周云蓬做过“一个盲人歌手在绍兴的文化生活”采访,并为他的《绿皮火车》作序。柴静在序中说:“他不与什么对抗,它就是要按它的一股子天性自在地长。”
四
读周云蓬的民谣,常惊异于他的独特视角,像生命力很强的植物,挣扎出朴素与艳丽。他的歌词风格呈现了两个不同的向度,一是向内追寻,一个是向外求渡,温柔花开是他,低眉忧伤是他,凛然仗义是他,狂放不羁也是他;有一双似乎比正常人更细的眼睛“看”世界,骨子里有一种决绝的进入,自由穿越在听觉与想象之间,将许多幻想融汇其中,那些无法用眼睛看到的画面与场景,在“沉默如谜”的气息里,翻新出为常人少见的景象,对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也有另类发现的惊喜。
酷爱读书的他,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尤其喜爱中国古典诗词,自刘邦、项羽,至建安七子、李杜、欧阳修、柳永他都能娓娓道来。除了“听书”,“听电影”也曾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一首自传性质的歌曲《盲人影院》中写道:“有一个孩子,九岁时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他描述一个剧院的情景,“四面八方的座椅翻涌,好像潮水淹没了天空”;他如此浪漫地表达情绪,“这是夏天最后的一个黄昏,河边的水草忙着结婚生子”;他写心目中的《山鬼》,“夜露是她晶莹的泪光,那时爱情正栖息我心上,晨星是她憔悴的梦想,那时爱人已长眠在他乡”;而一首《空水杯》,则在简洁中写出了沧桑:
孩子们出门玩儿还没回来,
老人们睡觉都没醒来,
只有中年人坐在门前发呆,
天黑了,灯亮了,回家吧。
孩子们梦见自己的小孩,
老人们想着自己的奶奶,
只有中年人忙着种粮食,
只有中年人忙着种粮食 。
长出来又衰败,
花开过,成尘埃,成尘埃。
长出来,成尘埃,
花开过,成尘埃。
十年流水成尘埃,
十年浮云,成尘埃。”
如果觉得他周围全是黑的,没有视角意象,那是对一个盲人写作者的极大误读。周云蓬说“有人觉得我写个“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好像就不正常,但实际上盲人的世界不是没有色彩的,人有一种心理上的视觉,不然你怎么闭上眼做梦还能看见东西呢?词语,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即使你没有见过红色,我告诉你红色这个词,你也会在自己心里描摹出一种东西来”。写作,让他找到了和音乐相通的表达方式。
他在这方面的特殊表现,让人想起另一位受人尊敬的残疾人作家史铁生。也巧,周云蓬曾在一篇《只身打马过草原》文章中,用多个细节表达他对史的理解。2010年12月30日,他在南京参加民谣跨年度的演出,天气很冷,没有去参加朋友的酒局,蜷宿在宾馆里早早睡了,“然而,这样一个岁末的冬夜,有两个亲切的生命收拾好行襄,悄悄地掩好门上路远行了。12月31日凌晨,作家史铁生在北京逝世”。
史铁生有“轮椅硬汉”之称,在小说《遥远的清平湾》中,他将艰苦的农村插队生活写得如诗如画,充满了情感,身体残疾的他有如此文笔和心态,着实令人敬叹。他后来的作品多了些对命运的沉缅与冥想,史铁生曾调侃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周云蓬也幽默自己:“我是世界壮丽的伤口,伤口是我身上奔腾的河流”,足见他们都是有强大生命气场的人。从而也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残疾人,要么弱者一脸苦难,要么强者一副深沉的样子。忽然觉得,喜欢周云蓬的一些作品,其实与喜欢他的生命状态有关,这一条奔腾不羁的生命,让他的音乐有了诗意、温度和力度。
五
爱上音乐是周云蓬的命,人的一生往往围着一个动机转。音乐,也是第一句重要,有一个旋律动机的时候,这首歌的命运就注定了。周的创作是鲜活、直率且充满人性的,让人感受到强大的生命磁场。现在有多少人把创作看成是生命的一部分呢?然而,感动人的音乐,就是扎根在流淌的血液中。
许多年轻人喜欢民谣,是因为民谣里有真诚的声音,大处把脉了时代,小处击中了人性,有痛感,焦灼感,有不羁与叛逆,有自由与渴望,有温情与血性;在民间点燃蓬勃的阳光,发出一道道冲破沉闷的光芒。
最初在西方兴起的现代民谣,在日渐开明和开放的中国有了较好的发展契机,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较宽松时期。当时,以高晓松为代表的校园民谣,出现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一批好作品,但周云蓬认为它最大的问题是“所有都是不变的三拍子,好像校园民谣就是青春气息这点东西,并没有反映出真正的校园。”
当人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啊,愿你降临!简单如一把吉他的民谣,也许技术的要求相对较少,但不能少的是现场荡漾的真诚与力量!周云蓬喜欢鲍勃•迪伦,喜欢唱《答案在风中飘扬》的这只老白兔,也喜欢崔健、罗大佑,称他们是“在大时代的转弯的涡浪里化而为鸟”,作品承载了大规模的集体潜意识。他把自己与小河、万晓利、野孩子、赵牧阳等人的音乐称为“新民谣”。与高晓松等人校园民谣的最大区别,就是“新民谣”带有强烈的草根性与社会现实感,因为“我们更多是在城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环境中挣扎的人。”
我们一直强调歌词的重要性,在周云蓬眼里觉得并不是特别看重的问题,如果一首歌的歌词比较优秀,它还是有缺陷,不叫一首歌。好的雕塑在罗丹那里就是把手砍掉的。一首歌是一个整体,像鲍勃•迪伦,如果他的那些歌旋律不好,歌词写得再好也没用,传播不出去,歌词写得好,顶多是一个文本,整体音乐是需要传播、需要旋律的。
作为既填词又谱曲的周云蓬,这样的理解是自然的,但也恰恰表明歌词在一首歌里同样具有的重要性,它是不能割裂的一部分。当你细心倾听一首好歌时,在漂亮的乐句牵引下,正是歌词部分直接击中了我们内心柔软的部分,并引发绵延的情思。好歌词让一首歌有了持久流传的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