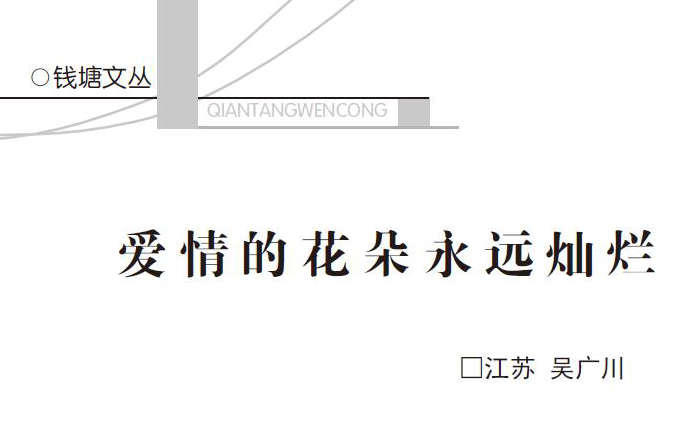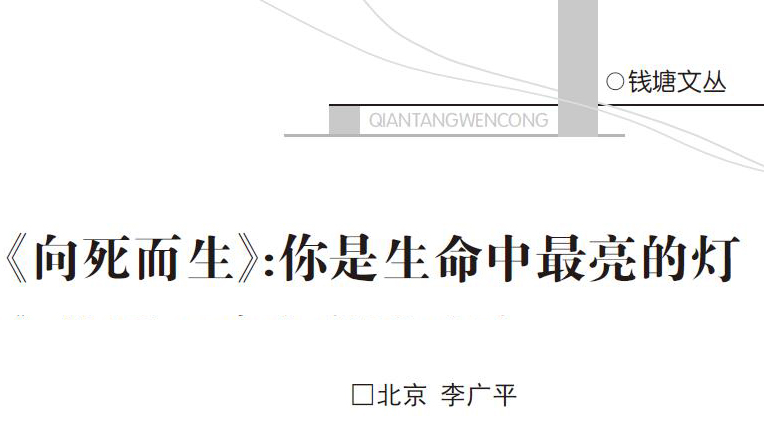《蝴蝶》:现代歌词的破茧之作

对于中国的歌词界来说,今年——2017,也许是个很有点纪念意味的时间节点——就在一百年前的1917年,有一位叫胡适的人在一份名为《新青年》的杂志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一首题为《蝴蝶》的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新青年》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创办,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许多早期中共党员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其重要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而写这首诗的胡适先生,则是一位大名鼎鼎学贯中西的文化名人。
好,关于《蝴蝶》的作者胡适和发表的杂志《新青年》,凡是中国人都知道,这里点到为止,无须我再来赘述。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这首白话诗《蝴蝶》。
说实话,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欣赏这首顺口溜一样的“五言诗”,怎么看也不见得有什么高妙之处,实在算不上什么“佳作”。可在一百年前的当时,却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壮举,革新派为之喝彩叫好,而守旧派则将其视作洪水猛兽,纷纷批评:“白话诗无甚可取” ,“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 。并嘲笑胡适的白话诗,好像儿时听“莲花落”一样,找不出一点诗味来……
可以想见,胡适当时开创的白话新诗还是有点挑战勇气的。
然而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后来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也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当胡适的第一首白话文新诗《蝴蝶》诞生之时,就宣告着从此古典诗与现代诗的分道扬镳花开两枝并必将各放异彩!如今,这首《蝴蝶》,早已被公认是中国新诗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影响巨大而久远!
那么问题来了——众所周知,作为歌曲的文字组成部分——歌词,也属于诗歌范畴(“能唱的诗”),既然《蝴蝶》是中国的第一首新诗,那么它对于歌词的意义又怎样来理解和定位呢?
就让我们用现代音乐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评判这首《蝴蝶》吧。你看:口语化、节奏感、韵律性……这不正好符合一首歌词的全部特点吗?因此如果说《蝴蝶》就是一首“能唱的诗”——歌词,完全名正言顺实至名归!把它交给100个作曲家可以谱写出100首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调性的优美旋律,然后交给100个歌唱家用不同唱法不同音色不同感觉去演唱。
然而也许是我闻寡见,至今我还没有没有发现过《蝴蝶》的任何歌曲版本。虽然不知何故?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已经完全具备了一首合格歌词的全部要素。这在他与《蝴蝶》一起辑入《白话诗八首》发表的另一首《希望》中可以得到佐证——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首诗后来经台湾乐人陈贤德、张弼谱曲后改名为《兰花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台湾歌星刘文正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港台地区歌星们竞相热唱的国语单曲。当时内地歌手苏小明、董文华等也将此歌作为她们的保留曲目并录制了盒带。近年来,随着群众性广场舞的盛行,《兰花草》歌声伴着大妈大嫂的舞步节奏再度唱响——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尝。
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
看得出,《兰花草》在谱曲与传唱的过程中对原诗的词句《希望》有些改动。而这并非是对原诗的某部分否定,而恰恰反证了人们对《蝴蝶》文学性与歌唱性结合得如此和谐完美的肯定和喜爱。这就像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在不断的流传岁月中,歌词和旋律都出现了多种版本,差点连作者也无从知道了,成了“青海民歌”。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见到歌曲《兰花草》署名为胡适作词的已经很少,多为“佚名词曲”,或干脆标明“台湾民歌”甚至“台湾高山族民歌”。记得有位大作曲家说,如果自己的作品被人当作民歌,那是他莫大的成功和荣幸!胡适及其《希望》即《兰花草》,正是如此。
这些,一百年前的胡适当然不会预料到,他当时想到的只是:“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倘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而他更大的“快事”则是:他的白话文诗《蝴蝶》“数年之后”不但引领了中国新诗潮流,而且也歪打正着的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歌词范本。
那么,那时候的歌词是什么样子的呢?追根溯源从诗经乐府到宋词元曲,直到胡适的《蝴蝶》之前,都是古典文言文体。我现在只举一首“极致”为例,下面是民初的所谓“国歌”《卿云歌》,其歌词为——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
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
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
这样的“歌词”,看来只有国宝级的国学大师才能懂。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四万万中国同胞绝大多数还是文盲。
当然,自古以来也有浅显易懂的歌词,那就是不计其数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民歌小调、市巷俚曲和戏曲唱词。不过这在当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胡适与他白话文新诗的出现,正是当时的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阳春白雪文化与社会底层下里巴人文化,在不断碰撞、交流后的绝佳绝妙融合!
于是,《蝴蝶》破茧而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蝴蝶》出现,在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中就很有点开先河意义了,文学史把1917年胡适发表《蝴蝶》作为中国白话文新诗的诞生的依据,说它是划时代之作,我看也并不为过!
诗歌如此,歌词亦然。为更全面了解当时胡适的新诗,我这里再从他1920年出版我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新诗集《尝试集》选录几首——
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
调寄《生查子》·相思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艺术
我忍着一副眼泪,扮演了几场苦戏,
一会儿替人伤心,一会儿替人着急。
我是一个多情的人,这副眼泪如何忍得?
做到了最伤心处,我的眼泪热滚滚的直滴。
台下的人看见了,不住的拍手叫好——
他们看他们的戏,那懂得我的烦恼?
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显而易见,这些新诗都具有非常强的可唱性,将其归入歌词门类一点也不牵强!只不过那时候要大家“多研究些问题”的胡适,其实很可能自己也根本没有去研究“歌词”这个“问题”。
胡适的新诗对我国现代歌词创作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最有代表性的是过了几年相继出现的《学堂乐歌》和《北伐军歌》,并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一些红军歌曲。这些歌大多采用西洋歌曲旋律或中国民间音乐填词而成,所填的歌词在文体、风格、语言、结构等方面基本上都明显受到胡适及其追随者们新诗的影响,这里不一一列举。
自《蝴蝶》始,中国新诗百年,中国现代歌词也百年。《蝴蝶》,真的就像美丽的蝴蝶一样破茧而出,翩然而飞,飞了一百年,并还将继续飞舞在中国诗歌与歌词的领地!
值此《蝴蝶》诞生百年之际,混迹于歌曲作者队伍中的我,真的好有一阵为之谱曲的冲动!然而冷静下来一想,由于蝴蝶的斑斓艳丽,写蝴蝶的歌已经太多了——《化蝶》(何占豪、陈钢曲、阎肃填词)、《思念》(乔羽词、谷建芬曲)《蝴蝶泉边》(季康词、雷振邦曲),还有与胡适《蝴蝶》最早题目同名的流行歌《两只蝴蝶》(牛朝阳词曲)……都是大师级作品,再加上毛阿敏、庞龙们的倾情演绎,要多好听有多好听,早已深入人心!——我知难而退!谱曲?打死我也不敢了! 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