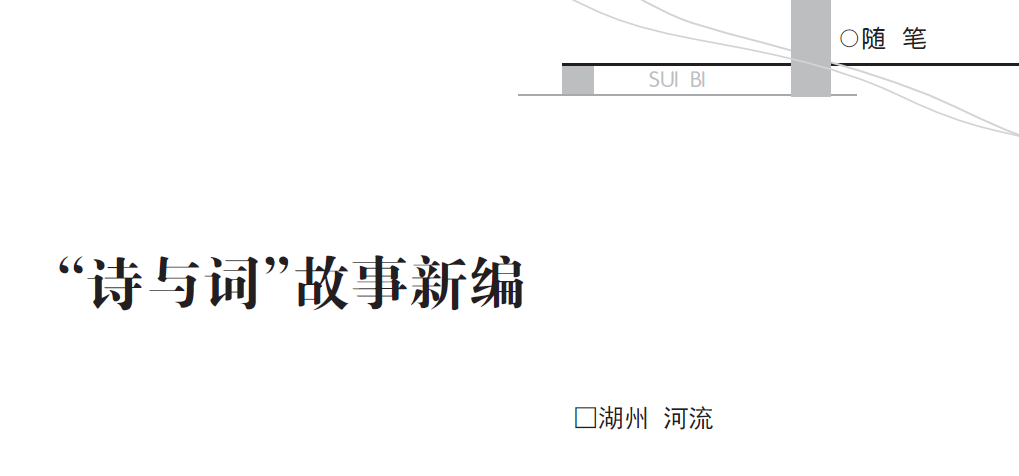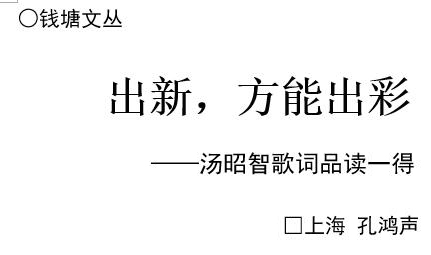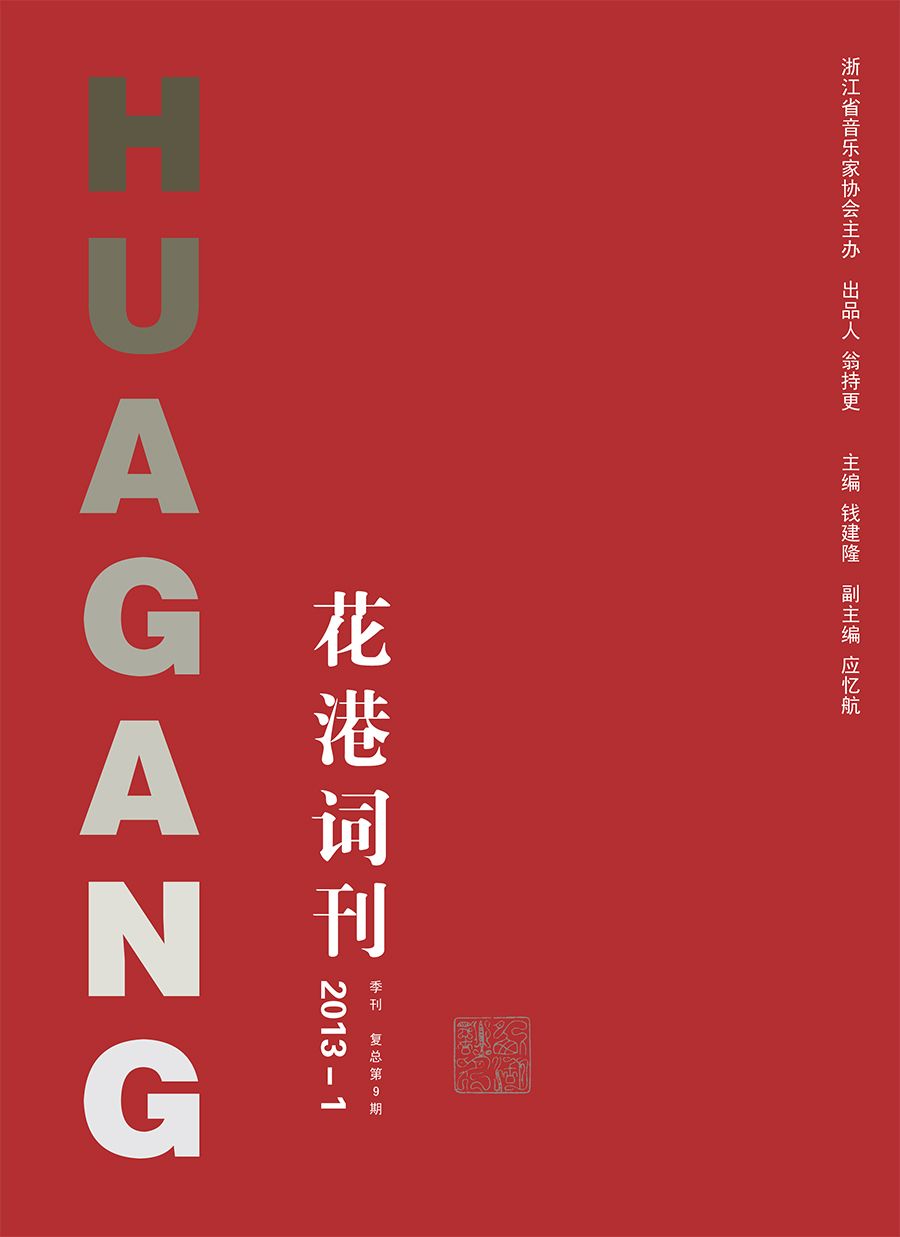“卷首语”引发的闲言碎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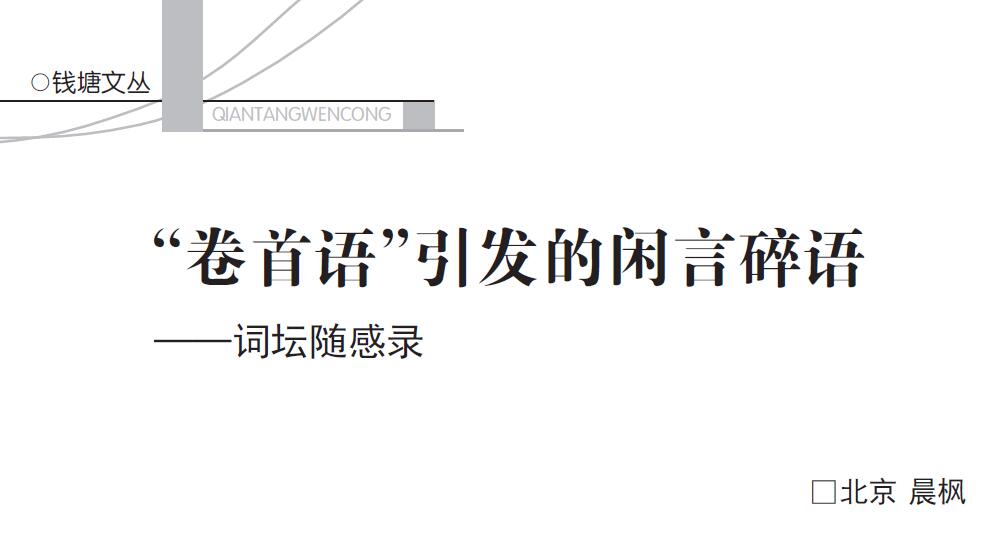
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一种习惯,每每阅读图书与杂志时,总喜欢先品读扉页的“前言”,或者翻阅末页的“编后语”,最后才去读正文。这样的习惯是好是坏,未曾考虑过,但如今已是积习难改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汉语出版物除了多卷本的图书之外,大体上置于正文前面的多被称为“序”、“序言”、“导言”、“引言”等,而置于杂志扉页的一般被称为“卷首语”,也有的没有“卷首语”,最后却有“编后语”或者“编后记”,其作用大致相似。
当下的歌词杂志,公开出刊的、内部出刊的,官方主办的、私人主办的,月刊的、双月刊的、季刊的、不定期的,统统加起来大概也就是十种左右吧,但每期开设“卷首语”栏目者却为数寥寥。我以为,刊物的“卷首语”虽则文字不长,但既是该刊物为读者打开的一个有风景、有引力、有温度、有诱惑的窗口,是一把度量这个刊物编者们水平与学识的一把隐形的尺子。一般来说,“卷首语”大多内容丰厚、文笔凝练,有观点、有见解、有阐发、有启迪,能够引人思索,令人赞叹,它会展现出编者的知识储备、艺术见地、行文风格以至人格魅力。因此,有没有这个窗口以及读者透过这个窗口能够看见、感受到的究竟会是什么、又有多少,这其中的文章实在不可小视。
当下歌词刊物中能够看到的“卷首语”,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编者每期专门挥笔撰文,二是从其它报刊杂志与各种书籍上遴选短文,三是在“卷首语”或“刊首语”的栏目下,刊发其它文字,比如获奖消息等等。三种情况除了第三种属于形同虚设、名不副实之外,其它两种均值得赞赏,只不过,我更倾向于第一种。理由在于,歌词刊物,是专业刊物,其读者对象包括歌词作者、曲作者与音乐爱好者以至文学爱好者,他们翻读刊物多是为了从中能够看到优秀的歌词作品,要么为其谱曲,要么直接有助于自己的歌词创作,因而,越是能够尽可能贴近他们的需求,就越能受到他们的喜爱。从这一点出发,编者亲手撰写的第一种“卷首语”显然要比从别的报刊上选取文章的第二种其优势更加明显,更加贴近读者的需求,基于此,我尤其赞赏浙江音乐家协会出刊的《花港词刊》的“卷首语”。
一家以季刊形式出刊的专业歌词刊物,在我们当下的歌词刊物中独一无二,不仅每期内容丰富、栏目多样、有词有歌,而且远离炒作、庄重致雅、自成气场,尤其是“卷首语”,每一期都传达着不同的艺术思考,显示着独特的艺术秉性。仔细品读你会发现,编者在短短的千字文里,往往会就当下颇受关注的某种歌坛现象引发出一段话题,而后,就此话题联系到当今歌词创作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地予以批评,正面阐发自己的某种艺术观点,最后,还就编选本期主要作品时的一些感受、体悟,言简意赅、推心置腹地向读者予以表述。我想,这样一篇深藏编者犀利目光、睿智见地并通过诗化的抒情文字精心编织而成的“卷首语”,因为有观点、有思想、有引导、有批评而一定会受到读者喜爱。
我之所以赞赏这样的“卷首语”,是由于钦佩编者没有就歌词看歌词、就歌词论歌词,而是在当今多元文化的时代语境中,把自己编辑的刊物看作一种具有富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奉送给读者的,这就使得“卷首语”有着高屋建瓴般的独特意义了。一本杂志的“卷首语”虽则并不能成为一种文体,但值得赞赏的“卷首语”由于作者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独具性灵、不拘格套,或评论思潮,或臧否人物,或针砭时弊,或推介佳品,都会让人犹如品读一篇精妙的千字文般具有莫大艺术引诱力,优秀杂志的“卷首语”可以积累成一册图书,供人赏析,而这样的例子即使在当今也并不罕见。
这里,我想起了1987年,当代著名诗歌批评家杨匡汉*先生曾在《词刊》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歌词文化的现代选择》的文章,文中曾这样写道,“在肯定这些年歌词创作的前提下,恕我直言,从前进意识着眼,目前歌词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或者说,它自身面临着某种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就多数歌词而言,还没有超越题材层而进入情理层,没有超越再现层而进入意蕴层,没有超越再现层而进入表现层,没有超越单纯的“号筒”层而进入审美层。一句话,还停留于惯性的歌词观念层,而没有进入探索富有现代意识的文化观念层……正由于上述原因,我愿意用‘歌词文化’的概念来代替目前流行的‘音乐文学’的概念。”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回头再来咀嚼这些文字、冷静品味这些文字所包容的内涵、所阐发的观点,我觉得依旧深刻精辟、发人深思,尤其是“歌词文化”这一概念,对于歌词艺术的历史传承与未来发展的现实意义,尤为言近旨远。
但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在歌词界不仅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领会、研究,更不曾在实践中予以有益的探索,相反,我们不少作者与编者却正是凭借“歌词就是音乐文学”的招牌沾沾自喜、自以为是——貌似身在文学艺术圈里,但极少甚至根本既不去品读文学,也不去走进音乐,更不去学习历史、哲学等等。所以,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一方面,相当多的作者们只是一味热衷于写词、发表、获奖,千方百计炒作自己,拔高自己;另一方面,一些编者们也是埋头刊载作者们的歌词新作,再辅以作者的近照、艺术简历、获奖情况等,偶尔刊发一两篇评论某位作者的“优秀”新作,也只有词汇华美的褒扬、捧场,找不到商榷,更不要说批评了,至于编者对于所刊发作品则因心中无数只能只字不提,更谈不上对整个歌词界以及歌坛的事件、思潮的评介了。所以,才会引诱出在极端愚昧无知中,将当今健在的作曲家奉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创始人”,从而将八十年前曾经产生国际影响的历史一笔勾销;也才会在无端自我膨胀中,利令智昏地将自己捧为“歌词巨匠”、“流行音乐教父”等等令人为之汗颜的咄咄怪事的出现。不难想到,长此以往,我们刊物编选出的歌词同自媒体自发问世的歌词作品与评论的区别究竟还有多少?歌词应有的文化品位与美学品质还会存在吗?
本来,歌词作为一种文化,在我国有着内在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基因,姑且不说始终同音乐未曾分离过的诗经、楚辞、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散曲、小令等等我国古典文学的旷世经典,就是从20世纪初随着我国近现代歌曲出现逐渐兴盛起来的歌词,也挺立着如李叔同、黎锦晖、刘大白、刘半农、田汉、韦瀚章、安娥、孙师毅、光未然、塞克、贺绿汀、公木、贺敬之、乔羽等因业绩昭昭而名垂史册的歌词大师,他们与一批伟大的作曲家相互合作所留下不朽传世之作,足以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长廊里,竖起一座近现代歌词文化的丰碑。
先辈为我们留下如此丰厚的精神遗产,确实值得我们去珍视,去继承,去充实自己,去提高自己。记得,2012年在广东梅州举行的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年会上,因故未能到会的乔羽先生在贺信中说过,“相信通过几代歌词作者的努力,中国歌词将会像我们祖先已经做过的那样,成为一代文学艺术的新景观。”简短的一句话,充满了先生对于前人们所创造的辉煌业绩的倾心敬慕与对歌词成为文艺园地文化新景观的热切期待。因为,歌词的经典与传世之作,是我们的前人创造的,而当代歌词如何在文化审美层面上去传承历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付出的还很多很多。我坚信,当我们刊物上所发表的能够进入民族文化层面和富有现代意识的歌词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卷首语”也必然能够日益牢牢吸引读者眼球。